在边疆驻守七年,我和走私毒品的团伙交火无数次,几次险些丧命。
终于,在最后一次行动中获得了走私团伙的成员名单。
就在我要将名单解码上交的前一秒,我被搭档的匕首穿透胸膛。
陷入黑暗前的最后一秒,我听见他对着外面大喊。
“江砺风就是就是毒贩的卧底!他在销毁证据!还想杀我灭口”
我的尸体被他草草扔在雪山下,他对外宣称我已经叛逃。
一夜间,我从人人尊敬的军人变成了人人唾弃的叛徒。
我的家被人泼上红漆,光荣之家的牌子被砸毁。
甚至连父亲的墓碑都被人推翻。
而我的未婚妻,怀着我的孩子,嫁给了我的搭档。
五年后,因为雪崩,我的尸体终于重见天日。
......
风裹着冰碴子砸在脸上时,我才意识到自己 “醒” 了。
不是从温暖的被窝里醒,是从雪山下那五年暗无天日的冰冻里。
挖掘机的轰鸣声震得我骨头缝都疼,铲斗把我从积雪里挖出来的瞬间,刺眼的阳光让我晃了神。
“这是......”
驾驶位上的老周声音发颤,他扒着铲斗边缘,盯着我蜷缩的骸骨,手里的操作杆都在抖,“不像是石头啊。”
我飘在半空,看着自己身上裹着的、早已看不出原色的工装。
这是我当年最喜欢的一件,耐磨防风,左胸还缝着哨所评 “先进个人” 时发的布标 —— 那是我用三次三等功换来的荣誉,现在却只剩一道模糊的线。
陈默跳下车的那一刻,我心里猛地一揪。
这小子是我带出来的最后一个兵,当年我 “叛逃” 时,他还在新兵连哭鼻子,说要跟着我守边疆。
现在他长大了,肩膀宽了,眼神也亮了,可看到我这副样子,他还是下意识地攥紧了对讲机,指尖冻得通红。
“指挥中心!K37 路段发现疑似人体骸骨,请求支援!”
半小时后,那道我恨了五年的身影出现在雪地里。
周砚山穿着笔挺的常服,胸前的军功章在雪地里闪着冷光,刺眼得很。
他蹲下来,用树枝拨我身上的布料时,我看见他眼底飞快地掠过一丝慌乱,快得像错觉。
“看这衣服材质,像是几年前的户外工装,”

他的声音和五年前一样,带着故作沉稳的沙哑。
“可能是迷路的驴友,雪崩时没躲过去。”
陈默皱着眉,我知道他在怀疑。
这小子心思细,当年我教他辨认装备时,特意提过这种工装的细节 —— 袖口的加固线、衣襟的暗扣,都是哨所定制的样式。
他的目光落在我胸前那道模糊的线痕上,眉头皱得更紧了。
可周砚山很快打断了他:“小陈,你去清点一下工具,别落下东西。”
我跟着陈默走了几步,又忍不住飘回担架旁。
两名战士小心翼翼地抬着我往临时帐篷走,我的胸骨处传来一阵熟悉的钝痛。
五年前,周砚山的匕首就是从这里扎进来的,带着冰冷的恶意,把我从 “江队” 变成了 “叛徒”。
帐篷里,临时赶来的法医正戴着手套检查我。
他剪开我腹腔的皮肤时,我屏住了呼吸 —— 那里面是我吞进肚子里的名单芯片,五年了,不知道还能不能使用。
“这是什么?”
法医的声音带着惊讶,他用镊子夹起那块冻硬的东西,外面裹着一层腐烂的组织,可芯片的金属边缘还隐约能看见。
就在这时,帐篷门帘被掀开,周砚山走了进来。
他看到托盘里的东西时,脸色瞬间沉了下去,像是被雪冻住了。
“不过是块铁片,有什么好检测的?直接按意外死亡处理,赶紧送走。”
“可是周队,” 法医有些犹豫,“这骸骨的胸骨有明显的锐器伤痕,不像是意外死亡...... 而且这‘铁片’的形状,看着像某种存储设备。”
“边境上迷路的驴友多了,遇到野兽、摔下山崖都有可能,哪来那么多他杀?”
周砚山打断他,语气里的威严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
“赶紧处理,别耽误公路抢修进度。”
就在这时,帐篷外传来陈默的声音,像一道光劈进黑暗。
“周队,省厅的法医到了!说是接到举报,过来重新检测骸骨!”


![[灵脉劫:三界归一]小说无删减版在线免费阅读_韩枫韩雪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8a85a77711d78bd5ac9afb9dbfe80ffe.jpg)
![[安然无恙]小说后续在线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9940d95cc41d7a99cbdd2ae2b6e9957a.jpg)

![蚀骨危情:重生娇妻狠又飒完结_[林薇薇林晚]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image-cdn.iyykj.cn/0905/26b8587d0382ee68f16468f8e32c86eff1e38110d1b34-CUp65i_fw480webp.jpg)
![[我于人间守长生]后续超长版_[陆昭林见鹿]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7ba1f0fba0a7a454038d471f6b3445a8.jpg)
![港综:我的系统能兑换茅山道法番外_[顾佳阿布]后续大结局更新+番外](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0c83ccfa107040098068193423ca2f6.jpg)


![[前男友成为上司后,逼我给他做小三]无弹窗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5bece6355571c91621f21ed120c6c1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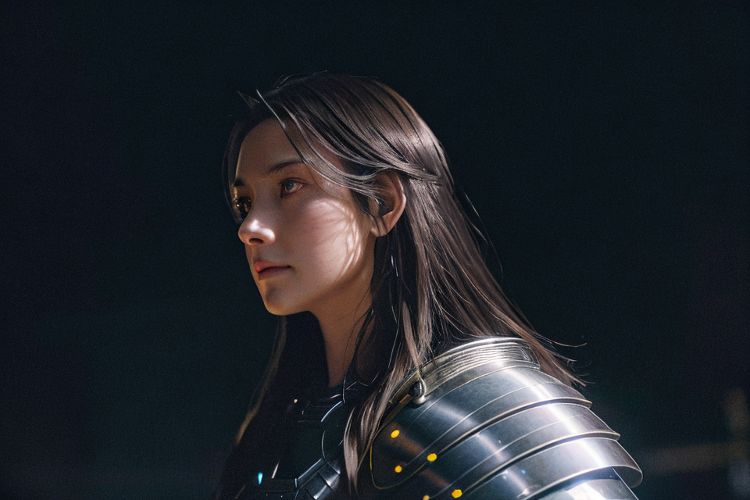




![[带崽错嫁绝嗣军官后被团宠了]全文+后续_「乔依张燕」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image-cdn.iyykj.cn/0905/e1de688af353aa8f630851ceba96de39e1aa2f2118bba6-psSfis_fw480webp.jpg)


![[订婚宴上,我多了个老公]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88e631b57257bef9046dff5f30d179a.jpg)

![[从清北退学后,赖在宿舍的假瘫妈悔疯了]更新/连载更新](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73e56ac8a4b61a84f4eba18b445290c.jpg)
![[未婚夫送堂妹生日礼物,我选择退婚]小说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064640f2232c59d1fc6a3e4f9b433fe.jpg)
![「老公让我把主卧让给白月光」全文免费无弹窗阅读_笔趣阁_[霍言澈宋清瑶]最新章节列表](https://image-cdn.iyykj.cn/2408/f9ba7b4239b8e3d9744588bbe69afab3.jpg)

![大秦:我的变强方式是夺宝完结_[嬴政王语嫣]全文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6a9b32bff35845c4335e89ce901d9a23.jpg)

![我掌握反弹伤害卡后,杀疯了后续完整大结局_[温俊林晚晴江暮雪]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dd47ed5db418e2f77f956640905121a2.jpg)






![[重生后,我笑看未婚夫被金丝雀毒成废人]最新章节列表](https://image-cdn.iyykj.cn/2408/55edbce2be1fbc4e936e0e89e547f1d6.jpg)




![[赌城夜魂]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林彻赵先生]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34cb55d2fcab6611a81bec742d7b265.jpg)

![[未婚夫为白月光悔婚后,我在牌桌上教他做人]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s://image-cdn.iyykj.cn/2408/84ba2c16c6a16bb339d983b02a0029bc.jpg)
![[七月半我家多了个陌生人]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2092ede69f0792bb986911145d60435.jpg)
![[妈妈头七刚过我接到了她的托梦]小说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47dbb6919c287e301549fe210d71fb4.jpg)





![[从捞狗屎开始的彪悍人生]后续超长版_[安平王兴贵]小说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3f83c015e22d627d9ee8139adacdfeb4.jpg)


![[女儿被校霸欺辱后,我拨通了卫星电话]完结版全文](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be5a9066f6a8f3bd34b801db9313f90.jpg)
![[穿书后,我和恶毒女配HE了]完整版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f0ebdacdf5362283a05a57302c0a3aa.jpg)

![高硕重生之大明合伙人全文+后续_[高硕朱元璋]全文+后续](https://image-cdn.iyykj.cn/2408/30ac1939b53069e3e1ed33100971968d.jpg)



![[且听风吟,静待花开]后续已完结](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1f20f757b4444ffb4b988b153a441c4.jpg)
![[梦醒惊碎满星河]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104cd3e997c75eb3a2a97c33f5c2451.jpg)


![[鹊桥难修,百年重渡]全集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7c115f49c00747b62364a2fb1e13955.jpg)

![[被当街抓小三挨打后,我让赘婿悔疯了]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e4c89a0bbea6c4d97085fde17f3f599.jpg)

![[假千金是死装姐,对不起,我超社会]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31a8e6a7745eae4239fc31963dd27e1a.jpg)

![[我氧气管被拔后,身为医科圣手的妈妈后悔了]后续全文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f93e3f964ac5efe692deca6a7d5242b.jpg)

![[妈妈的生日礼物我不要了]电子书_「小琪」全文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74ccd17671fc8f38e3fdda2742e6a874.jpg)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