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当天,我刚结束一场救命的手术,却因为脱力在车上睡了五分钟。
匆忙赶到家时,爸爸脸色阴沉。
“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团圆的日子让你妹妹等你一个人,她身体不好你不知道吗?”
我累得眼前发黑,只想坐下。
“爸,我刚下手术台,连着做了十八个小时——”
爸爸把碗重重一放。
“楚微,你以为自己当个破医生就了不起吗?”
“救人救人!我看你真是救人救魔怔了!你妹妹的病你怎么不救?”
“要我看,你就是自私!拿着医院那点死工资,半点不如你妹妹会讨我们欢心!”
“这饭你别吃了,赶紧去给你妹妹炖汤!”
他把我推开,扶着妹妹回了房间。
我知道他是想逼我妥协,用我妹妹那根本不存在的病绑架我。
但这次,我只默默拿起手机,拨通了院长的电话:
“院长,我同意了。请马上安排我加入援非医疗队,为期两年,即刻出发。”
1.
电话那头,院长明显愣了一下,随即是掩饰不住的欣喜。
“微微,你可想好了?这可不是去旅游。”
“我想好了。”我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那扇门里,是我爸,还有我那体弱多病的双胞胎妹妹,楚染。
门外,是我。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连站都站不稳的“不孝女”。
挂掉电话,我脱下高跟鞋,赤着脚走进自己的房间。
十八个小时的高度紧张,我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极限,此刻只想倒头就睡。
房门被猛地推开,爸爸的脸因愤怒而扭曲。
“楚微,你刚才给谁打电话?你是不是又想躲出去?”
他身后,楚染扶着门框,脸色苍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仿佛随时都会倒下。
“姐,你别生爸的气了,都是我不好,我的身体太不争气了。”
她说着,眼圈就红了,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
我看着她,只觉得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疼得快要窒息。
这套表演,我看了二十年。
从十岁那年,她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开始,我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我不能大声说话,怕惊扰她。
我不能吃零食,因为她闻到味道会“呼吸困难”。
我学了医,因为爸爸说,家里有个医生,楚染就多一分保障。
我进了心外科,成了全院最年轻的主刀医生,只为能亲自“拯救”我的妹妹。
可她的病,却越来越重。
重到除了我亲手熬的汤药,什么都吃不下。
重到我必须放弃所有晋升机会,守在市立医院,守着她。
爸爸见我不说话,火气更大了。
“你看看你妹妹!你再看看你!铁石心肠!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冷血的东西!”
“姐,你别走,你走了我怎么办?”楚染哭着扑过来,想抱我的腿。
我下意识地后退一步,躲开了。
她的身体僵在半空,眼里的泪水凝固了,取而代代的是一丝错愕和怨毒。
那眼神一闪而过,快得让我以为是错觉。
这时,门外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我的未婚夫,同为心外科医生的言烬走了进来。
他看到屋里的情景,眉头微蹙,随即换上温和的笑容。
“叔叔,怎么了这是?微微,你又惹叔叔生气了?”
他自然地走到我身边,揽住我的肩膀,语气里带着亲昵的责备。
“小染身体不好,你多让着她点。”
爸爸看到他,脸色缓和了些。
“阿烬,你来得正好!你评评理,这丫头刚回家就要闹着去什么非洲!她妹妹怎么办?这个家怎么办?”
言烬的身体明显一僵。
他揽在我肩上的手,骤然收紧。
2.
言烬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带着探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微微,叔叔说的是真的?你要去援非?”
我没有回答,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他眼里的温和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复杂的,我看不懂的情绪。
“胡闹。”他松开我,声音冷了下来,“研究项目进行到关键阶段了,这时候走,前功尽弃。”
“是啊,姐,”楚染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走到言烬身边,怯生生地拉着他的衣角,“烬哥的项目那么重要,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她的声音又恢复了那种柔弱无辜的调调。
我看着他们,一个是我准备托付终身的男人,一个是我血脉相连的妹妹。
他们站在一起,看起来才更像是一对璧人。
而我,像个多余的闯入者。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我拉开衣柜,开始收拾行李。
“楚微!”爸爸的咆哮声在我身后炸开。
一个玻璃杯砸在我的后脑勺,碎裂的声音尖锐刺耳。
我有一瞬间的恍惚,紧接着,我伸手摸了摸头,只摸到一手的血
“你要是敢走,我就死给你看!”
楚染配合地发出一声惊呼,身体一软,就朝着言烬的怀里倒去。
“烬哥……我……我心口好疼……”
言烬立刻抱住她,满脸焦急地回头看我。
“微微,快!快看看小染!”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所有人眼里都只有那个无病呻吟的楚染,却忽略了满头是血的我。
从小到大,从来如此。
看到我的血,爸爸明显愣了愣。
下一秒,楚染又开始喊痛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去,而我只是淡淡的找出医药箱处理了一下伤口。
把血止住后,我拉起了地上的行李箱。
我的行李箱里,只有几件换洗的白大褂和几本厚重的医学专著。
爸爸冲过来,一把夺过我的箱子,狠狠摔在地上。
“你妹妹都要死了!你还在弄你这些破烂玩意儿!”
“我说了,让你去给她炖汤!你听不懂人话吗?”
他指着我的鼻子,唾沫星子都快喷到我脸上。
二十年来,第一次,我没有顺从。
“她没病。”
我的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空气仿佛凝固了。
爸爸愣住了。
言烬抱着楚染的手臂,也僵住了。
楚染靠在言烬怀里,那张苍白的小脸上,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姐……你……你说什么?”她颤抖着问,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委屈。
“我说,你没病。”我重复了一遍,目光直直地刺向她,“楚染,你的心脏很健康,比我的还要健康。”
“你胡说!”爸爸最先反应过来,一个巴掌扇了过来。
我没有躲。
火辣辣的疼痛在左脸颊上蔓延开,头也更痛了。
“你这个疯子!你为了能自己出去快活,连你妹妹的病都不认了?”
“阿烬,你告诉她!你是医生,你告诉她小染的病有多严重!”
言烬的脸色很难看。
他看着我,眼神里是失望,是责备。
“微微,别闹了。小染的心脏确实有杂音,不适合情绪激动。你快跟她道歉。”
心脏杂音。
是的,生理性的心脏杂音,百分之三十的健康人都会有。
这个被他们当作主要依据的“诊断”,是我亲自下的。
那时我刚进医院实习,爸爸逼着我给楚染做检查。
我告诉他,楚染很健康。
他不信,闹得整个科室鸡犬不宁。
最后,我只能在诊断书上,写下了“生理性心脏杂音,建议静养”这几个字。
从此,这成了楚染的护身符,也成了套在我脖子上的枷锁。
我看着言烬,突然觉得很可笑。
“言烬,你是心外高材生,你看过的病人成千上万,你真的觉得,她是病人吗?”
3.
言烬避开了我的视线。
他扶着楚染,让她在沙发上坐下,柔声安慰。
“好了好了,不生气,你姐姐就是工作太累了,胡言乱语。”
楚染靠在他肩上,小声地啜泣,身体一抽一抽的,看起来可怜极了。
我爸则直接冲到我房间,将我的护照、身份证件一股脑地翻出来,死死攥在手里。
“我告诉你楚微,只要我活一天,你就别想离开这个家!”
“你的证件我没收了!我看你怎么走!”
他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
就像过去二十年一样,用亲情和责任编织成一个笼子,把我牢牢锁在里面。
我没有去抢,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爸,补办证件只需要十五个工作日。”
他的动作停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第二天,我照常去医院上班。
左脸高高肿起,五个指印清晰可见,头上也缠了一圈绷带,引来了不少同事探询的目光。
我只说是不小心撞到了门。
刚换好白大褂,护士长就一脸为难地走了进来。
“楚医生,你爸爸……他在你办公室,说要等你。”
我心头一沉。
推开办公室的门,爸爸正坐在我的椅子上,一脸的理所当然。
他见我进来,立刻站起身。
“你跟我去院长办公室,把那个什么援非给我退了!”
“我不去。”
“你!”他气得扬手,但看到我脸上的伤,又悻悻地放下了。
“楚微,你非要闹得这么难看吗?家丑不可外扬,你不知道吗?”
“是谁在闹?”我反问,“是谁跑到我的单位,影响我工作?”
他被我堵得说不出话,脸色涨成了猪肝色。
办公室外,已经有好奇的同事在探头探脑。
他大概也觉得丢脸,压低了声音。
“你妹妹昨天一晚上没睡好,今天早上就咳血了!你再这么刺激她,她是真的会死的!”
咳血?
我学医八年,从来不知道心脏病会导致咳血。
他为了留下我,已经开始满嘴胡言了。
“那你应该带她去看呼吸科,而不是来找我。”
我说着,就要把他往外推。
他死死扒住门框,开始耍赖。
“我不走!你今天不答应我,我就不走了!我就住在你这儿!”
“让你们医院所有人都看看,你楚微是怎么对待自己亲生父亲的!”
正在这时,言烬走了进来。
他手里提着一份早餐,看到我和爸爸在拉扯,立刻上前。
“叔叔,微微,你们这是干什么?”

他把我们分开,将早餐放到我桌上。
“微微,你脸上的伤……叔叔也是一时情急,你别往心里去。快,先吃点东西,你昨天到现在都没进食。”
他摆出一副体贴入微的模样,好像昨天那个冷漠指责我的人不是他。
我爸也立刻换了副嘴脸,对着言烬诉苦。
“阿烬啊,你快劝劝她,她这是要我的老命啊!”
言烬叹了口气,转向我。
“微微,援非的事情,我们能不能从长计议?我知道你想救人,但也不急于一时,对不对?”
“小染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你这一走就是两年,她怎么办?叔叔怎么办?”
他打出感情牌,一句一句,都踩在我的痛点上。
我看着他,看着他眼中恰到好处的担忧和深情。
如果不是昨晚回家,在楼下看到他把车钥匙塞给楚染,听见楚染娇声对他说“烬哥,这车好漂亮,比姐姐那辆好看多了”,我可能真的会动摇。
那辆新提的保时捷,是我准备给他的惊喜。
我攒了很久的钱,想在他生日那天给他。
可他却提前从我爸那里知道了,带着楚染,先去享受了这份“惊喜”。
而我,像个傻子。
爸爸还在一旁煽风点火:“就是!阿烬对你多好,你妹妹也离不开你,你怎么就这么狠心?”
办公室门口的同事越聚越多。
他们交头接耳,对着我指指点点。
想必在他们眼里,我已经成了一个为了前途抛弃病重家人,连未婚夫都留不住的冷血怪物。
爸爸见状,更是来劲,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
“我没法活了啊!养了这么一个白眼狼女儿啊!”
“她妹妹都快死了,她还想着自己去国外风光!天理何在啊!”
他的哭声尖锐又刺耳,反复切割着我的尊严。
言烬皱着眉,伸手想去扶他,却被他一把甩开。
“微微,你看这……要不你先跟叔叔回去?我们好好谈谈。”
他把所有压力都推到我身上,让我来解决这个烂摊子。
就在这时,楚染的电话打了过来。
言烬接的,开了免提。
“烬哥……我好难受……爸爸是不是在姐姐那里?你让他快回来……我怕……”
楚染的声音气若游丝,充满了恐惧和依赖。
爸爸一听,哭得更凶了。
“我的女儿啊!我的小染啊!是爸爸没用,留不住你姐姐……”
言烬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看着我,目光里满是失望和谴责。
“楚微,你一定要这样吗?”
“小染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所有人都看着我。
我的父亲,我的未婚夫,我朝夕相处的同事。
他们都在等我低头,等我妥协,等我像过去二十年一样,咽下所有委屈,回去当那个“伟大”的姐姐。
我深吸一口气,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
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我拨通了急诊科的号码。
“喂,急诊吗?这里是心外科楚微。”
“门诊大楼A座801办公室,我父亲,楚建国,疑似急性应激障碍,伴有暴力倾向和自残行为,请立刻派人过来处理。”
“另外,通知住院部,准备一张床位。我妹妹,楚染,病情‘突发’,需要立刻住院,进行全面检查。”



![[假千金说全家霸凌她,我断供她却悔疯了]最新章节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d6fd57c24a84bf8359f7d092f7c2840.jpg)









![[妻子诈死和竹马逍遥快活,重生后我成全他们]后续完整大结局](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a22e814518deeaacf88a6259cb5d6b7.jpg)



![[闺蜜死后,我改写了人生]后续全文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37db571609a70ac97512a2fd8f4d4ea.jpg)

![[萤火焚尽于长夜]全文免费无弹窗阅读_笔趣阁](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16df6b1eeac2e43572f1b01048ce6c5.jpg)

![[霸总妈驾到统统闪开]全章节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d035c06d6de6f7304182e5c03c9f7f24.jpg)

![必归令抖音小说_[怀远苏氏]后续全文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1e9adc62ba651e11a87936875fd39a2b.jpg)

![[老公爱惨的白月光回国后,我主动离开]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http://image-cdn.iyykj.cn/0905/419d42421f0a158d037df71d83fd7761e2dcd6a420817b-ouqpjW_fw480webp.jpg)
![[恋爱纪念日男友要过三人约会,我直接分手]全文+后续](https://image-cdn.iyykj.cn/2408/f0f5ad17162482336d743fe9d87a1769.jpg)
![[读档重来99世,我先给自己注射癌症病毒]后续已完结](https://image-cdn.iyykj.cn/2408/6470e086bb91bbd8362d071f44a8a16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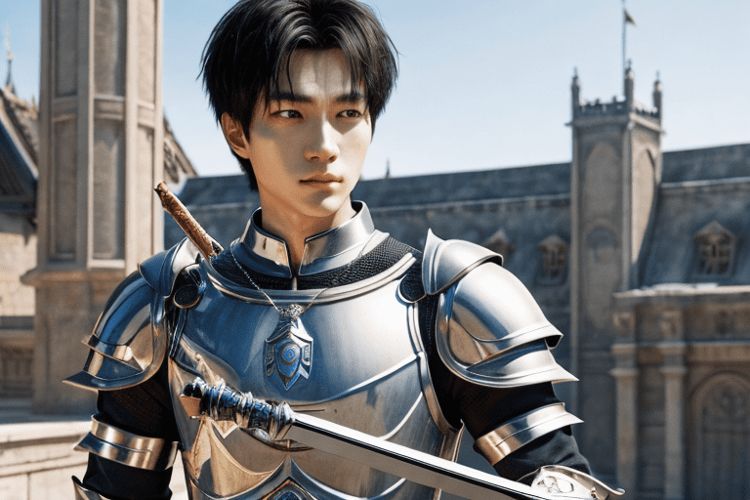
![[背叛我的未婚妻,最后却一无所有]小说无删减版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d7adfb52c8278e21f7d8729fd9d6e4d.jpg)
![都市灵狐:我的修仙日常不太对劲后续已完结_[林晚星玉佩]大结局](http://image-cdn.iyykj.cn/0905/65f1653d5dfb1e7a2f2e43b0a6402108b1c6f47ea8bc4-VzoTr8_fw480webp.jpg)
![[勾引鬼差后,我重回八零成全冷情状元郎]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s://image-cdn.iyykj.cn/2408/942c5f1996af27c49e138fdcf225d4bc.jpg)

![[末世开局:我怀了黑化男主的崽]后续无弹窗大结局_[苏晚陆时衍]抖音小说](http://image-cdn.iyykj.cn/0905/b54a3d5b013237a891e695a68832dcf3ef7914d62144ab-XtFq9q_fw480webp.jpg)


![[重生七零嫁硬汉,渣男前夫后悔了]全文完结版阅读_青青阮念后续更新+番外](https://image-cdn.iyykj.cn/2408/d39c86b3c351b6ece766f67fcaf7f401.jpg)
![[未婚夫和秘书续火花364天,我转嫁竹马首富]小说后续在线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0a4bd85943348b342f05ecb7d3cf673.jpg)




![[神君换娶婢女后,他毁疯了]完结](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36db04f47cb03637ef3ad4e67d80978.jpg)
![[阁老父亲认回我后,害死儿女的夫君哭求复合]番外](https://image-cdn.iyykj.cn/2408/d28453fa2ca88ba56b49dc1b01f4d2c0.jpg)
![[被举报停职后,骂我媚男的学生悔疯了]完结版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07113166aa466fdb732c2e7a011a982.jpg)

![[毒夫又如何]抖音小说](http://image-cdn.iyykj.cn/0905/265aebe59fdf82050b7e8c4ad3f08b1c6db7afa21e5390-JVQXpI_fw480webp.jpg)
![[社畜穿越后,我靠吐槽修仙]小说免费在线阅读_[林风玄机]全集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3b5700a664cf6f6f5b72347c51fce67b.jpg)

![[法盲父母逼我捐肾,我反手送他们上热搜]后续完结版](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e377b264a23498b6b22c81503a1d995.jpg)












![「重启的假期,重启的爱」完结_[楚颜季晨]全集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d0a82eec47c99c821eb52b67b5b59a4e.jpg)



![灵异故事:驱鬼人全文完结版阅读_[林默李月]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b183c18a9bb74b2fec48a4e886d0927.jpg)
![「死者是我怎么可能」小说免费在线阅读_[林羽微微]小说无删减版在线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a047b6a11cd9c132e7fd2deab9316f3.jpg)

![[雪落无声,镜花无迹]更新/连载更新](http://image-cdn.iyykj.cn/0905/18bbb24ca62811684c86a16f1cc8e6d8c56e8c0810b954-y3uN9Q_fw480webp.jpg)

![[顶流影后直播追夫火葬场,可惜我已经死了]大结局](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aa8023e46a1311093a795df33bc2a62.jpg)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