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君成为大理寺少卿,打马游街的那一天,
我被鬼市的野狗啃去了大半个脑袋。
红色的官服在太阳下耀眼夺目,
我的尸体在阴暗的鬼市里长满蛆虫,散发出难闻的恶臭。
直到被人发现时,
他才知道,躺在他面前面目全非的女子,是整个大秦的暗探首领,
在敌国隐忍负重五年,传回来了无数的情报。
官居高位的他执意要亲自验尸,
想要为死者正衣冠,全其形;
可是他从我尸体上发现当年定亲时一起绣的手帕时,
却僵在了原地。
他猛然想起来,他那通敌叛国的妻子,
已经流亡他乡、消失整整五年。
01
林煦白握着量骨尺的双手微微颤抖着,
他翻检着尸体,目光却时不时瞥向我的右手手腕,
我知道,他在找我与生俱来的那块胎记。
我飘在半空中,苦笑着摇摇头,
他找不到的。
当年我远走他乡的时候,特意请民间的奇人异世改头换面过,
别说是我如今面目全非的尸体,
就是我活生生的站在林煦白面前,
他也未必认得出我。
“大人,可是有什么发现?”
手下的人见林煦白的脸色不对,小心翼翼的开口。
林煦白在我的尸体上来回看了又看,最后垂下眼眸,浅淡的回应了句:
“或许是我多想了。”
像是失落,又像是松了口气。
手下的人看着面前的尸体,眼底带着淡淡的敬佩和怜悯。
“属下在大理寺呆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遇见如此残忍的死状。”
这副尸体的头颅被野狗吃去了大半,
伤口处爬满了无数的蛆虫。
十指被折成了一个诡异的形状,双脚也被砍去,
就连五脏六腑,也各自碎裂多处。
唯有一颗快要干瘪的心脏,还算完整。
从最旧的伤口一直到致死伤,时间整整跨越了大半年,
也就意味着,这副身体,至少承受了半年的折磨。
林煦白的呼吸渐渐急促了起来,
他的手在那仅存的小半张脸颊上验了又验,触摸上下颌的那一瞬,双手蓦然一僵。
【记:死者生前有削骨的经历,时间大概在……五年前】
属下忍不住开口:
“大人,我听说朝廷派出的暗探,大都会请民间的异人剔骨换面。”
“抹去身上显眼的标志。”
“这位姑娘会不会……”
林煦白的眼角骤然一缩,再看向我的尸体时,眼底多了几分复杂的情绪。
飘在半空中的我顿了顿,面前突然有些迷蒙。
我在鬼市连续游荡了几日,
记忆也渐渐开始退散,
但我记得……我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林煦白冷硬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快去查,务必找到五年前为人剔过骨的异人!”
我一路跟着林煦白,飘飘晃晃的回了家。
家里依旧是五年前我离开的模样,唯一不同的是,
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此刻被打扫的一干二净,
全部换上了另一个女子的物品。
我看着干净的庭院,
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我已经,整整五年没有回家了。
余莺莺见林煦白回来,贴心的为他准备好了饭菜,
见他脸色不太好,她试探着开口:
“我听说,鬼市新出了一桩命案。”
“死者的身高年龄都跟虞鱼差不多……算来算去,她也有五年没有消息了吧。”
林煦白身体一僵,再开口时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厌恶:
“别跟我提她!”
余莺莺的手中的帕子紧了又紧,她咬咬唇:
“可是……阿鱼毕竟也曾是你的妻子……”
我看着她这副欲说还休的模样,只觉目眦欲裂,数不清的恨意从胸腔蔓延。
她也曾是我最好的手帕交,可是半年前如果不是她出卖了我的身份,
我也不会是今天的下场……
“她不配。”
林煦白的声音中明显多了几分起伏,却也依旧冰冷,
他的话让我陡然顿住,
心口涌出说不尽的酸涩。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便是认识她。”
02
我知道年少时期的林煦白很喜欢我,
也知道现在的他,恨我恨到了骨子里。
我和他相识于微末,是师出同门的师兄妹。
七岁那年,我被送去名门大家那里学艺,学武功谋略,学机关奇门,也学探案勘验,
也就是在那时,我遇见了林煦白。
他总是一个人,沉静的做好所有的功课,
招式练了一遍又一遍,跌倒再爬起、再跌倒再爬起……
可后来我才知道,
那个沉默寡言的少年,全家都战死在了敌国的铁骑之下。
他这一生,最恨北疆。
十余载春秋冬雪,我陪他在那个梅花树下,
将所有的功课温习了一遍又一遍。
知道我们成亲,直到五年前,
北疆王子耶律齐入秦,
被众人发现时,我躺在耶律齐的床上。
他红着眼尾,声音颤抖:
“阿鱼,我知道这都不是真的。”
“只要你说,我就信你。”
那时候我看着他紧皱的眉头,忍不住嗤笑一声:
“林煦白,就是你看到的这样。”
“我不喜欢你了,想换一个玩玩儿。”
“很难懂吗?”
他的眼睛里带着不可置信,他指着耶律齐,
“阿鱼……为什么是他?”
“你知道的,我平生最恨北疆人。”
我冷冷地一摆手,眉眼间带着戏弄和讥讽:
“知道又如何?”
“是你林家死在了他们的刀下,又不是我虞家!”
“你恨他,关我什么事?”
他双目猩红地看着我,双拳紧紧地攥在一起,
落在了我身后的床板上。
最后,他气急而去,只留下我,跪坐在床上沉默了许久。
眼泪划过脸颊,心中是无限的绞痛。
我和耶律齐越走越近,
林煦白也红着眼劝了我一次又一次。
可我看向他时,却再也没有了当年眉眼弯弯的模样。
再后来,为了给耶律齐接风,宫里特意举办了宴会。
那天我在自己的里衣里藏了一把匕首,准备入宫行刺。
林煦白察觉出了我的意图,从背后紧紧得抱住了我,声音里是数不尽的哀求:
“阿鱼……别去好不好?”
“你若是做了,这辈子便回不了头了。”
“求你……”
我听他一次又一次的哀求我,却始终冷着脸无动于衷。
他双手抚上我的小腹,
“阿鱼……我知道你怀孕了,就当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好不好?”
心脏像是被细针扎了一下,
可我还是抬起头来,笑魇如花。
“你想多了。”
“孩子不是你的。”
我至今都记得他那时的表情,震惊、愤怒、哀痛、不可置信……
我转身离开,身后响起他悲哀的声音:
“阿鱼……你真要为了他做到这种地步?”
我身子顿了顿,却没有停。
后来因为林煦白,我最终没有行刺成功。
那时他站在皇帝的身侧,看向我时眼底时数不尽的恨意和冰冷。
我被下了死牢,等待秋后问斩,
他也始终没再看我一眼。
从那之后他恨极了我,却不知道在他走后,皇帝亲自扶起了我:
“朕知道你受了委屈。”
“你放心,等你回来那日,朕一定还你一身清白。”
那天京城的风雪,足有一尺厚。
思绪渐渐拉回,我看向半夜坐在房顶的林煦白,他将自己喝了个烂醉,
他手里紧紧攥着那方手帕,看着天边的月亮,让人猜不透在想什么,
良久,他才慢慢吐出一句话:
“虞鱼,我恨死你了。”
我透明的双手穿过半空,想要抚平他紧绷的眉头,
可我的手指缩了缩,最终还是收了回来。
算了……
如今的林煦白,大概不喜欢我碰他。
我看着他,张张嘴想告诉他什么,可是话到口中时,
我又有些想不起要说什么了。
天色既白时,捕快急匆匆地赶来:
“大人,我们找到异人了!”
03
我没有再跟着林煦白去查看我的尸体,五年未见,我想再多看看家里。
我在府里四处游荡着,最终去了我当年的卧房。
它已经完全荒废了,
余莺莺站在那棵梅树下,眉眼间有着说不出的阴骘。
一个相貌普通的男人站在不远处。
“我们扔在鬼市的尸体被发现了。”
余莺莺的红唇像是嗜血的蛇信子,
“我知道。”
“还是林煦白亲手验的尸。”
“我猜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痛恨的女人,被他亲手解剖了。”
全身翻起巨大的恨意,
我发了疯一样,想杀掉她,可是透明的双手穿过她的躯体,我伤害不到她分毫。
或许我的怨念太重,无端的,余莺莺也觉得身上有些凉。
当年,我奉旨离京,前往北疆去做一名暗探。
临行前,余莺莺找上了我。
她哭红了眼睛,说我不该那么傻,明明我留在京城也有大好的光阴,
为什么要去做那暗无天日的暗探。
那天我拦着她没让她把实情告诉林煦白。
我说:
“等我回来吧。”
“万一我……死在了北疆,他也不会太伤心。”
后来我隐忍负重五年,终于拿到了那份最重要的情报。
可是当夜,暗桩被铲除,我和一众手下,一共有三十五名死士,
全部在那夜被捕。
那晚的鲜血浸在雨中,染红了整整一条街。
那日为首的人,便是余莺莺。
我至今都记得,当时的余莺莺拿着刑具,一件一件,全部用在了我的身上。
意识昏迷前,
她对我露出阴毒的笑容。
“虞鱼,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还改头换面,来了北疆……你放心,你很快就会永远消失在这世间了。”
我张张嘴,干涸的嗓子里发不出半个字。
可我依旧朝她瞪着眼睛,拼命地想要质问她,
到底是为什么!
明明她是我儿时最好的手帕交,是我最信任的人!
也是因为这样,
当时临行前她认出我时,我才没有反驳她。
她知道我所有的痛苦,知道我身上新添的每一处伤口,
也知道我每每想起林煦白那失望的眉眼,
彻夜难眠。
可是……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质问,老虎钳夹住我的十指,用力一掰。
十根手指瞬间断裂,折成了诡异扭曲的形状。
和着我凄厉的惨叫,她的声音像是地狱里的毒蛇:
“不这么做,林煦白他怎么彻底忘记你呢?”
“虞鱼,你不会还想着,等任务执行完回去跟他重新开始吧……”
她突然凑近了我,声音轻轻的:
“做、梦。”
下一瞬,我的双膝被她用铁锤狠狠的砸下。
暗无天日的刑房里,她阴冷的笑着。
“对了……虞鱼。”
“你拿到的那份情报,藏哪儿去了?”
情报……
我张张嘴,突然看向余莺莺,想起了那件很重要的事情。
于是我片刻也等不及的,朝着大理寺的方向飘去。
04
停尸房里,林煦白带着皮套的双手微微颤抖着。
他开始了对我的第二次验尸。
内室里,是当年为我改头换面的异人。
他年纪已经很大了,记忆也不太好,
可他还是结结巴巴地,
回忆着我当年的模样。
一旁的画师听着他的描述,开始一笔一笔画下我当年的样貌。
我飘在一旁,看着林煦白从我的尸体上查出一条条线索,心中说不出的酸胀。
还记得当年我还和他开着玩笑:
“师兄啊,验尸这门功课学不好没有关系。“
“等我以后死了,我把我的尸体留给你来练手。”
他弹了一下我的脑袋,瞪着我嗔怪道:
“瞎说。”

回过神来后,我有些急切。
想要拉住林煦白。
“林煦白!”
“腰腹的那道伤口,快!”
“剖开它,里面有东西!”
林煦白检查着我的双手突然一顿,似有感应的,
指腹抚上了我腰腹的一处旧伤口上。
那是我第一次用刀剑时,不小心自己划的。
当时我哭了整整两日,
它也是我身上的第一道伤口。
可是如今,那道伤口又在半年前添了新伤,将旧伤完完全全的覆盖住。
我的心脏开始发紧,忍不住开口提醒他:
“林煦白,你剖开它。”
“快点!”
里边,是暗桩被拔除之前,我留下的情报。
心底的不安又迅速升了起来,
林煦白抚摸着那处伤口,用力地摇摇头,像是在否定自己。
“不是你……”
“肯定不是你。”
“虞鱼,你是叛君叛国的败类,她是为大秦忍辱负重的英雄。”
“所以不可能是你。”
他抖着手,重新切开了那道伤口。
半空中的我松了一口气,心底却闷闷的,像是塞了一团棉花。
片刻之后,林煦白从那处伤口内,剖出了一个小指大的竹筒。
他发现了……
“林煦白,将纸条放在烛火上。”
“就像我们以前做的那样……”
这是幼时我和林煦白偶然发现的一种方法。
将糖水当作墨汁,在纸上写下内容,
不过片刻便会消失。
再看时,需要放在烛火之上烤过之后才能显露。
林煦白看着那张空白的纸条,
心底的不安越发浓烈。
可是他还是,将字条放在了烛火之上。
字条渐渐显露出原本的字迹。
林煦白正要去细看纸条上的内容,捕快便拿着画像闯进了停尸房。
“大人!画像画好了!”
“是……是……是夫人……”

![[把爱意藏进风雪里]小说无删减版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10f7a0afba158441d335a5a32b4b55c1.jpg)

![[妈妈用我攒的钱买金首饰后,她悔疯了]最新章节在线阅读](http://image-cdn.iyykj.cn/0905/1b31ba7758d14e0a0d3d8872e1454afbe5be506d4bd81a-UaJh2y_fw480webp.jpg)


![[重生后,我阻止了老公听信佛牌]全文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108df23e6c976adf0b3f70eba91ef8b.jpg)
![[灵脉劫:三界归一]小说无删减版在线免费阅读_韩枫韩雪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8a85a77711d78bd5ac9afb9dbfe80ffe.jpg)
![[安然无恙]小说后续在线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9940d95cc41d7a99cbdd2ae2b6e9957a.jpg)

![蚀骨危情:重生娇妻狠又飒完结_[林薇薇林晚]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image-cdn.iyykj.cn/0905/26b8587d0382ee68f16468f8e32c86eff1e38110d1b34-CUp65i_fw480webp.jpg)
![[夫君要我给寡嫂让位,我让了他又后悔什么]全文+后续](https://image-cdn.iyykj.cn/2408/6c708b1532ba4226d615ae707995405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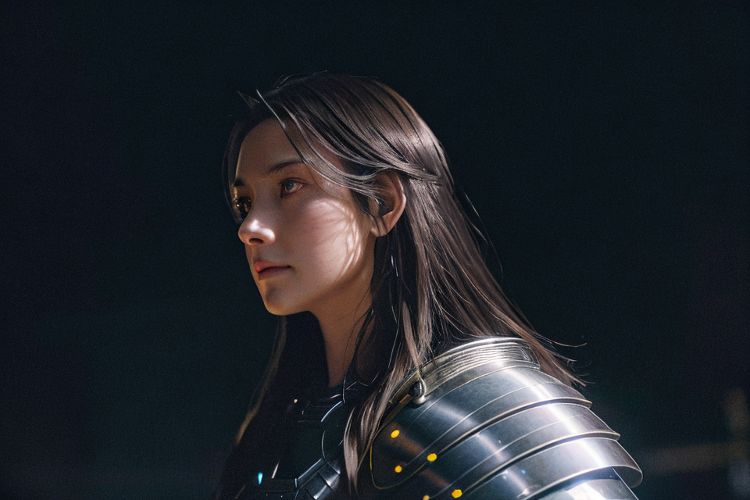




![[带崽错嫁绝嗣军官后被团宠了]全文+后续_「乔依张燕」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image-cdn.iyykj.cn/0905/e1de688af353aa8f630851ceba96de39e1aa2f2118bba6-psSfis_fw480webp.jpg)

![时沙之主:章海后续大结局更新+番外_[王经理章海]小说后续在线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d9124e794ba6eb73a949bf34133af8b9.jpg)




![[从清北退学后,赖在宿舍的假瘫妈悔疯了]更新/连载更新](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73e56ac8a4b61a84f4eba18b445290c.jpg)
![[未婚夫送堂妹生日礼物,我选择退婚]小说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064640f2232c59d1fc6a3e4f9b433fe.jpg)
![「老公让我把主卧让给白月光」全文免费无弹窗阅读_笔趣阁_[霍言澈宋清瑶]最新章节列表](https://image-cdn.iyykj.cn/2408/f9ba7b4239b8e3d9744588bbe69afab3.jpg)










![[朕的江山,画风不对]番外_周玄金銮殿番外](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4cfb878289a376980bf7b8ac9f84bf6.jpg)


![[女儿的书房被曝光后,全网炸了]后续更新+番外](http://image-cdn.iyykj.cn/0905/e7cc8a0c4c344c653d98c20a8faacc81ed55fa631c8901-7uFFnV_fw480webp.jpg)

![[赌城夜魂]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林彻赵先生]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34cb55d2fcab6611a81bec742d7b265.jpg)

![[未婚夫为白月光悔婚后,我在牌桌上教他做人]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s://image-cdn.iyykj.cn/2408/84ba2c16c6a16bb339d983b02a0029bc.jpg)
![[七月半我家多了个陌生人]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2092ede69f0792bb986911145d60435.jpg)
![「邪医觉醒:透视双瞳,银针定乾坤」后续完整大结局_[宿舍楼奶奶]最新章节列表](https://image-cdn.iyykj.cn/2408/d6cde018284c33574516e0ddd24a2f0a.jpg)



![萌宝碰瓷后,冷面总裁人设崩了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_[秦聿果果]完结](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12100b68106813272df0d4e6d31eb41.jpg)


![[从捞狗屎开始的彪悍人生]后续超长版_[安平王兴贵]小说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3f83c015e22d627d9ee8139adacdfeb4.jpg)

![港综:从掠夺靓坤开始全文+后续_[陈余阿华]最新章节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1b8eca6203079faec1f67255ed31afd1.jpg)
![翼上青空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林楷陈默]全集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12e297f4a06b90377e030f47c03fc3f0.jpg)

![[三个徒弟不顾我会变成吸血鬼,轮番欺骗我的救命血清]全集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118225d3268405950d65032f6c33e2a.jpg)

![三国:我是刘禅,我要续命小说全文txt完整版阅读_[刘禅刘备]最新章节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14f47ee311de973cdd538c8bbcd81bf1.jpg)




![[灵脉之吞噬成尊]后续已完结_[林辰王掌柜]完结版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8eaaea7234f389465b612c4e3785db12.jpg)
![[闺蜜想陷害我,我反手让她进局子]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de1a11c7e38d49bfbde4fc105cf52e7.jpg)
![[被当街抓小三挨打后,我让赘婿悔疯了]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e4c89a0bbea6c4d97085fde17f3f599.jpg)

![[假千金是死装姐,对不起,我超社会]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31a8e6a7745eae4239fc31963dd27e1a.jpg)

![[我氧气管被拔后,身为医科圣手的妈妈后悔了]后续全文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ef93e3f964ac5efe692deca6a7d5242b.jpg)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