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聚文斋就乱成了一锅粥。
天还没亮透,巷子里就有人扛着木牌走来走去,一边敲锣一边喊:“临川府今年春试——读书人都给我醒一醒——误时者,自误前程——”
掌柜一大早就拎着鸡毛掸子在走廊上巡:“都起来都起来!谁要敢给我赖床,到时候被主考赶出考棚,别说是住我店里的!”
刘仲迷迷糊糊翻身,刚想再抱着被窝滚一圈,就被楚南生一把揪住领子:“还睡?再睡就去阎王殿考去。”
“阎王殿不收文卷吧?”刘仲眼睛没睁开,嘴已经开始贫,“那地方不看字,只看账。”
沈砚已经起床,穿好衣服,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
考场只许带规定的笔墨纸砚,什么纸条、书本一概不许。沈砚把自己写过的练笔、抄过的案子全都翻出来,挑了几张写得实在不堪的,揉成一团扔进火盆。
“烧了?”刘仲心疼得坐了起来,“那可是你半夜熬出来的字。”
“写得不好,留着也是丢脸。”沈砚淡淡道。
被火舌舔到的纸卷迅速卷曲,黑灰飞起。火光一闪,将“人心”“人命”几个字映得极亮,随即又被火吞没。
楚南生看着那一点火,忍不住道:“要不……你还是少想点案子的事,先把心收回来写卷子。”
“卷子上也是问案子。”沈砚笑笑,“只是换了个说法,叫‘治乱之机’。”
刘仲叹气:“幸好主考老爷听不见你这句话,不然明儿一早就叫你去当师爷,不用考了。”
屋外传来掌柜的催促声:“备马的备马,走路的排好队——都给我看着自己的竹牌,别丢了!”
三人也不再磨蹭,各自背上包袱,拿好笔墨,推门下楼。
临川学宫前门已经炸了锅。
从城内城外来的读书人,穿得好一些的骑马而来,穿得一般的坐小车,再穷的就抱着竹匣子步行。到了门口,不论出身高低,都得乖乖排队,拿着自己的竹牌一人一人验过去。
门口搭了几张桌子,桌后坐着的是府里的小吏,手边摆着一本厚簿子。
“小名?”
“楚南生。”
“籍贯?”
“临川府。”
小吏在簿子上勾了一笔,把他的竹牌递回去:“进去,记得选自己院子那一列坐,别走错。下一位——”
轮到刘仲,他把竹牌递过去,小吏看一眼,嘴角一抽:“你这字写的,可真难看。”
刘仲脸涨红:“我文理好。”
“你若卷子也这么让人眼晕,别怪阅卷老爷。”
轮到沈砚,他如实报了籍贯:“清江乡。”

那小吏看了眼他的衣襟,又看了眼竹牌上的籍贯,似笑非笑:“乡下来的呀。”
沈砚只是拱手,不接话。
轮到进去搜身那一关,几个衙役排成一列,专查衣袖、鞋袜,防有人夹带小抄。
“袖子伸直。”
“鞋脱了。”
“腰带解开一点。”
刘仲一边被搜,一边小声嘟囔:“昨儿井边死了个人,他们倒不摸摸那井,光摸我们。”
那衙役瞪他一眼:“你要不想考,正好给你换一副镣铐戴戴。”
刘仲立刻闭嘴。
沈砚被搜得倒还顺利。那块半截铜片和抄下来的几行字,他昨晚就老老实实锁在书箱里,根本没带出来。
进了学宫大门,一眼望去,院子里搭满了考棚——一排又一排低矮窄长的木屋,每个间隔只够一个人坐下。门口挂着号牌,从一号一直排到看不见头。
“你几号?”
“西院三十五。”
“我四十,你前头不远。”
楚南生拿着自己的编号,眼睛在密密麻麻的棚屋之间晃来晃去,总觉得哪一排哪一排看起来都差不多。
刘仲在一旁给自己打气:“呼——这叫‘金榜前一点灯’,我们现在是灯里的油。”
“你这油还容易糊了。”楚南生道。
三人按照自己的编号,穿过一条又一条狭窄的通道。每条通道两旁都是紧闭的小门,门上留出一掌宽的缝隙,让监考的人可以从外面看到里面的光影。
走到西院三十附近时,沈砚的脚步慢了半拍。
就在三十五号之前,那里空着一个棚位。门上挂着的牌子写着:
西院三十四。
旁边有个读书人正往里安放自己的笔墨,见他们经过,抬头看了一眼,问:“你们知道这位的位子是不是留着的?”
他说着指了指对面那间紧闭的、没有灯光的小棚。
门上,竹牌写着三个字:
周成席。
楚南生眼皮一跳。
“应……该算是留着。”他勉强笑了笑,“总不能说换给别人。”
那人“哦”了一声,不再问。
三十五号棚位里只是两块木板拼出的三面围墙,一张窄窄的板凳,一块板子当桌。桌上放着一张空白的试卷,还覆着一块薄薄的纸。
沈砚走进去,放下自己带来的笔墨,转身把门关上。门一合,外头的嘈杂立刻被挡了一大半,只剩下模糊的人声和远处若有若无的敲锣声。
棚屋很窄,他一伸腿就能碰到前面,一回头就能碰到墙。
头顶是一条长缝,透着天光。
那条缝里,可以看见一小块灰白的云。
“又是这天。”沈砚心里想着。
与其说是天,不如说像一张毫无表情的纸,等着人往上写字。
考棚外,主考和几名副考已经坐在临时搭起的大堂里。
案上摆着朱笔,手边放着经书和几卷旧试题。
一名年长些的主考捻着胡须,看了一眼桌上的时辰簿:“时间到了?”
旁边的记时官答:“到了。”
“那就发题吧。”
铃声连着锣声一响,各院里负责传题的小吏一窝蜂似的跑出来,抱着一摞摞刻好的木板往各个考棚方向去。
不多时,每个棚位的门上一一传进一块木牌,木牌上用黑漆写着几行题目。
沈砚抬手揭开自己的那块。
上面写着:
“问:治一郡之乱,先理何事?
又问:刑名之设,以何为本?”
下面又有一行小字:
“兼以临川近事为引。”
看到这一句,大概所有临川人都懂——所谓“临川近事”,便是这几日闹得沸沸扬扬的井边人命案。
沈砚看完,不由失笑。
“老天爷不好好睡觉,也爱凑热闹。”
他提笔,在卷面最上端先写了姓名籍贯,又写了几行谦词,才落到正文。
笔尖落纸的第一句,却不是天子、圣人、刑书,而是——
“人命为重。”
他稍一顿,又在旁小小地添了一个字:
“本。”
——刑名之本,在于人命之重。
写完这一句,他才慢慢往下铺开,把这几日所见所闻、听老差役的故事、听街坊的议论、看钱道亨在堂上说的话,都一一拆开来,用那些规矩的典籍词汇包裹起来:
“官当如何临事不避嫌疑”“案当如何不轻信鬼说”“百姓何以会信鬼不信官”……
他写得很快,却不急躁。字迹谈不上多好看,却十分有力。
写到一半,他下意识抬头,透过那条长缝看了一眼。
一条灰云正在头顶慢慢压过,像一只巨大的手掌。
几乎在同一时辰,县衙后堂,钱道亨也在翻纸。
那是三年前的案卷。
卷宗的封皮上写着:“柳氏失踪案”。
下面一行小字:“疑投河,未见尸。”
这四个字,像虫子一样趴在纸上,看得他心里发痒。
卷宗翻开,头一句便是:“本县绣坊女子柳氏,年十七,三月初三夜后出门,未归。”
接着是绣坊掌事、坊中女工、柳氏邻居各自的供词:
“那日白天还好好的。”
“她手很巧,活计多。”
“听说有读书人常在巷口站着。”
再往后,是当时负责这案子的捕头笔录:
“派人沿河搜寻多日,未见尸首。坊中无人见其与人争执。询问读书人,皆称‘偶有所见,并无私交’。推断当是一时想不开,自投河中。”
结案意见只有寥寥两句:
“人证无,物证无。
暂以‘失踪’备案。”
钱道亨看得直皱眉。
“这是案子?这是打发烦人的纸。”
他忍不住骂了一句。
当年他刚到临川,这案子已经结了。那时候他事务繁多,也就按习惯翻了翻案卷,把这个“疑投河”的三字记在心里。谁知三年后,这三个字竟成了一口井旁所有传言的底子。
他翻到卷末,却发现有一张纸被夹得有点歪,似乎是后来加上的。
那张纸的字迹,与前面不同。前面的笔画圆滑,显然是老练写手,这一张却有些犹豫。
上面写着:
“柳氏之母胡氏,数次来衙门哭求,言姑娘心性不似自寻短见之人。
又言三月初三日,有人曾见柳氏在学宫后巷同一青衫郎说话。
此事未详。”
落款是一名小吏的名字。
钱道亨想了想,轻声道:“胡氏……就是昨夜井边那个老妪?”
这名字,和昨夜跪在井旁磕头的老太太对上了。
他敲了敲案,看向站在一旁的小吏:“这张纸,为何没写进结案意见里?”
小吏吓得一哆嗦:“回老爷,这是三年前的卷,属下……属下那时还没来临川,不知。”
旁边年纪大些的师爷咳了一声:“老爷,那会儿的知县大人,向来嫌麻烦。”
嫌麻烦——三个字,几乎是对不少案卷的最好注脚。
钱道亨手一翻,合上卷宗,眼中却多了一分冷意。
“嫌麻烦,把一条人命撵出门外。”
他忽又想到早上堂上那句——
“官若不替百姓做主,那还不如不做。”
说这话的,是那个叫沈砚的穷秀才。
“嘴倒狠。”钱道亨喃喃,“只是……也未必全错。”
他起身,把卷宗放到一边,吩咐道:“来人。”
门口的差役赶紧进来。
“去,把昨夜那个胡氏再请来一趟。”钱道亨道,“别吓她,就好声好气地说——本官要替她的女儿问一句‘为什么’。”
差役连忙应下。
考棚里,时间在一笔一画之间慢慢流。
有人下笔如飞,有人半天挤不出一句话,有人咬着笔杆,额头冒汗。
中途传饭的时候,有小厮推着车从棚外走过,递进一碗冷掉的饭和一点咸菜。
刘仲在棚里低声嘀咕:“这叫‘考饭’?这是喂猪。”
话虽那么说,他还是乖乖吃完——谁也不敢饿着进考场。
沈砚本来就吃得不多,略垫了几口,便又埋头写卷。
他把“临川近事”用了一整段写在卷末,却只写“某地井边有死案,城中传言多归于鬼”,一笔也没提“柳氏”两个字,也没提周成,只写“某生”。
他知道,这张卷子会被送到府城,送到主考手里,甚至可能送到更远的地方。
有人会从字里行间看他的心性,却不会真来替临川翻案。
“那就写给看得懂的人看。”
他在心里说。
夕阳西下,铃声再次响起。
“收卷——”
一声声吆喝从考棚外传进来。门缝被敲响,小吏伸手进来,让每个读书人把卷子交出去。
卷子一离手,沈砚心里莫名一空。
“好歹也是一张命换来的题目。”他站起来活动活动僵硬的腿,“看来周成也没完全白死。”
走出考棚,院子里一片倦态。
有人揉着腿,有人捶着肩,有人眯着眼看天:“终于完一场了。”
刘仲一出来就长长吐气:“我刚刚在棚里,觉得那板凳就是刑具。”
楚南生则还心不在焉:“阿砚,你卷子里……有没有写那口井?”
“写了几句。”
“你疯了?”刘仲瞪眼,“你这是拿主考当听书先生。”
“写得很规矩。”沈砚笑,“看不懂的人,只当是套话;看得懂的人,自有他自己的想法。”
三人正说着,院门口忽然有人大声叫:“沈砚——临川县衙有请!”
那声音很快压过了考后的闲谈。周围人不由得侧目。
“才考完就被传去县衙?”
“不会是卷子上写错话挨板子吧?”
“你少乌鸦嘴。”
楚南生和刘仲同时转头看向沈砚。
沈砚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看来书箱翻完,轮到翻人了。”
“我陪你去。”楚南生道。
“你还是歇着。”沈砚拍了拍他的肩,“该说的我会说,不该说的你也插不上嘴。”
刘仲却瞪着那名衙役:“就一个人?你们县衙是多缺人手?”
衙役被他说得一愣,挠挠头:“老爷只叫他一个。你们若要去当陪客,回头被老爷赶出来,别怪我没提醒。”
县衙后堂,灯火已经点上。
柳氏案卷摊在桌上,旁边还放着一碟新泡的茶,茶面上飘着一片桃花瓣——也不知道是从哪里飘进来的。
胡老太被请到堂下,战战兢兢地跪在蒲团上,嘴里还念叨着“不该劳烦老爷”。
“胡氏。”钱道亨淡淡道,“当年你姑娘失踪,是三月初三,对不对?”
胡老太点头:“是……是那天。那天她还跟我说,坊里的活干完了,要去庙里烧个香,求她今年能顺利攒够嫁妆钱。”
“她平日,可常去学宫后那口井边?”
“去。”胡老太叹气,“那条路近,从绣坊回家总要经过。她说那儿桃花好看,夏天还凉快。有时候她会在那里歇一会儿。”
“你可曾见她跟读书人说话?”
胡老太犹豫了一下,咬牙道:“见过几回。有个穿青衣的读书人,总在巷口站着,有时候帮她提提筐,有时候说几句话。老身远远看着,没敢过去吵她。”
“你没问那读书人姓甚名谁?”
“问过一次。”胡老太低头,“我那闺女说,他在外地读书,说不准能不能考中,将来若是飞黄腾达也不会忘了她。我一听就生气,骂她做梦,她哭了好一场。”
她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那之后没多久,她就……就不见了。”
钱道亨静静听完,才道:“当年你来衙门哭,说你闺女不会自己投河,可有人理你?”
“老爷……那时候的老爷,说案子已经结了,让我们认命。”胡老太用袖子抹眼,“老身没本事,只能认。”
她猛地磕了个头:“若不是老爷如今愿意再问一句,老身也不敢再提。”
钱道亨沉默许久,才缓缓道:“你先回去。以后有人再拿你闺女的名字编鬼故事,你就说——本官在查。”
胡老太连连磕头:“谢老爷,谢老爷。”
她刚被人扶下去,外头就传来通报声:“老爷,沈砚到了。”
钱道亨“嗯”了一声:“叫他进来。”
沈砚一进后堂,便看见那摊开的卷宗,还有桌上的那片桃花瓣。
“学生见过老爷。”
“不必多礼。”钱道亨摆手,“站着说话就好,省得一会儿又要跪。”
他打量了沈砚一眼:“今日考场可还顺利?”
“勉强把卷子填满了。”沈砚道,“题目出的……很有趣。”
“有趣?”钱道亨挑眉,“写‘临川近事’的那一行,你怎么写?”
“老爷真要听?”
“本官问的话,你就答。”
沈砚想了想:“学生写——‘近来某地井边有命案,众人多言是鬼,有官不愿细查,有人不愿细想。’”
“还有呢?”
“还有一句:‘百姓宁信鬼,不信官,病在前日,不在今日。’”
这话说得不轻。
钱道亨盯着他,忽然笑了一声:“你倒是敢写。”
“卷子上是写给不认识的人看的。”沈砚道,“他们若生气,也打不到我。”
“你以为真打不到?”钱道亨哼了一声,却没有再追究,“算了,本官叫你来,不是为了问卷子。”
他把案上一叠纸推过来:“这是三年前柳氏案的卷宗。你看看,有什么想说的。”
沈砚愣了一下,接过来翻了翻,神色很快就沉了下来。
“这案子……”他皱眉,“是被草草结了。”
“看得出来?”
“前后供词没有相互印证,连‘同柳氏说话的读书人’是谁都没查。”沈砚道,“只凭‘沿河未见尸’就写‘疑投河’,这不是查案,是赶人回去。”
他翻到那张后来加上的小纸条,念了一遍,抬头道:“写这张纸的小吏,还算有点心。”
“可惜,没用。”钱道亨道,“写归写,没写进结案意见里,那就是废纸。”
沈砚沉默了一会儿,问:“老爷如今翻这案,是打算……”
“你以为我打算什么?”
“学生不敢妄想。”
“本官只是觉得,既然这口井如今又出了人命,总该问问三年前有没有人借这口井做过手脚。”
他顿了顿,又道:“你既然嘴上不信鬼,那就帮本官找找看,这卷宗里,哪里最像人的手脚。”
沈砚低头重新看,目光一行一行划过去。
“首先……”他慢慢道,“柳氏失踪那晚,是三月初三。她母亲说,她本来要去庙里烧香,但邻居看见她,是在学宫后巷。”
“其次,她母亲说有一个青衫读书人常在巷口等她,可卷宗里却没有问一句那读书人是谁。”
“再次,沿河搜寻了三日,未见尸。若真是投河,水流那样急,该不会一个人都没看见。”
他说着说着,自觉嗓子发干,停下来喝了口茶。那片桃花瓣刚好漂浮在茶水边缘,轻轻晃了一下。
“所以?”钱道亨追问。
“所以——”
沈砚抬起头,“柳氏不一定死了。”
钱道亨点点头:“本官也是这么想。”
“那她去哪儿了?”
“这就是我们要查的。”
钱道亨把茶杯放下,声音低了半度:“周成与一位姓柳的女子有信往来,这一点你已经看到了。现在这案卷告诉我们,临川曾有一位绣坊柳姑娘在三年前失踪。若这两位是同一个人,那么——”
沈砚接道:“那三年里,她去了哪里?这次回来,又为何要在井边留痕?”
他脑子里忽然闪过那两封信里的句子:
“我搬出绣坊了。”
“井那边的桃花,我不去了。”
如果真是她写的,那么,她曾经刻意远离过那口井。
“老爷。”他脱口而出,“三年前柳氏失踪之前,有没有人见她在井边跟人争执?”
“案卷上没有写。”
“那坊里的其他绣娘呢?”
“你想去问?”钱道亨看着他。
沈砚意识到自己又往前迈了一步,有些不好意思:“学生只是问问。”
“问得好。”钱道亨道,“只是问这些,本官让衙役去就够了,何必劳烦你一个考生。”
他顿了顿,又道:“你今日考完第一场,接下来两日还有场次,不必日日往衙门跑。明日你安心写卷,后天再来。”
“那书箱——”
“周成的书箱,暂且封着。”钱道亨道,“等这几场考完,再看有没有新的线索。你那块半截铜片,也别随便拿出来。”
沈砚心里一紧:“老爷知道?”
“你以为本官只会看卷宗?”钱道亨哼了一声,“铜片上的纹路,本官看不懂,但知道不是普通玩意。世上多的是拿奇巧之物讨彩头的人,考前碰到这样的东西,不是吉兆。”
他挥了挥手:“行了,你回去歇着吧。本官也得歇一歇——明早还要照常开堂。”
“明早还开堂?”
“井边的案子还没结,当然要开。”
沈砚拱手告退,转身出门。
夜风一吹,院里那棵老槐树的枝条晃了晃,影子落在地上,像一只伸长的手。
他抬头看了一眼那段天,心里默默算着日子——
已是三月初四。
三年前的三月初三,一位绣娘消失。
三年后的三月初三,一位读书人收到了“不必再去井边”的信。
三月初四的凌晨,他却死在井边。
“是巧合呢,”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还是有人精心挑了日子?”
这一夜,临川城里灯火点点,各家各户关上门窗,准备迎接明日的第二场大考。
也有人彻夜难眠。
有人在磨墨准备卷子。
有人在翻旧案准备翻脸。
还有人,可能在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对着一半铜镜,慢慢勾出一抹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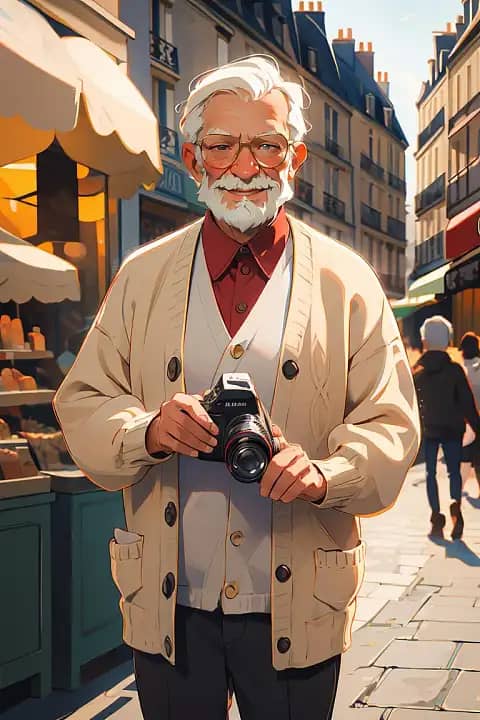


![[揭穿爸爸出轨后,我被妈妈塞进洗衣机]最新章节免费阅读-爱八小说](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7f5ee47e4a950ef0fae526247751c10.jpg)
![[雾里天涯,晚风将至]小说后续在线免费阅读-爱八小说](http://image-cdn.iyykj.cn/0905/5fdf8db1cb13495420bb7e08bd2f7b54d0094aa7.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