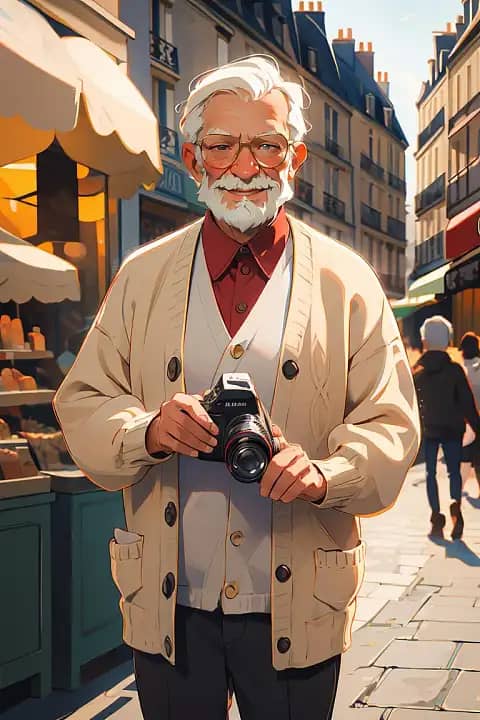井边的雨小了些,却没有停。
春夜的黑,被雨洗得发亮,井栏上的水珠一颗颗滚下去,落入井口,砸在看不见的黑水里,发出细微而持久的声响。
那口旧井本就年久失修,石栏被苔斑爬满,唯有临近桃树的一段,因为时常有人倚着乘凉,显得略微光滑些。此刻,桃树正开得浓,雨水把花瓣打得粉碎,一片片黏在井沿上,远远看去像是有人在石上洒了一层淡淡的血。

草席下的尸体安静地躺着。
钱道亨站在井旁,眉梢拧成一团,眼睛却不敢多往草席那边瞟。他不是没见过死人,做了这么多年官,枉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尸体都见过,只是今日的时辰不对,地点也不对——贡院开考在即,这样一副光景,最容易惹出“天不佑临川”的闲话。
“仵作呢?仵作怎么还没来?”他恼火地咳了一声,“叫你们去请人,是去睡觉了么?”
“老爷,仵作蔡三刚才说腿脚不好,脚一滑摔了,正让人扶着呢。”一个衙役小声答,“这会儿大概在路上。”
“腿脚不好就换一个!”钱道亨压着火,“平日里吃俸禄,真要他出力,就推三阻四。”
他边骂边往前走两步,脚下一滑,差点陷进泥里。旁边的小吏连忙扶住他,他才稳住身形,心里更是烦躁。
“把草席掀开。”他说,“先认认人。”
两名力气大的衙役对视一眼,伸手抓住草席边角,一鼓作气掀起。草席卷起半空,溅出几滴泥水,然后重重落回旁边地上。
尸体便完全暴露在雨中。
死者身量不高,穿着青色儒衫,腰间挂着竹牌,头发散乱,半浸过水,贴在脸侧。脸色因溺水发白,双唇略青,两只眼睛大睁,瞳孔已经散掉,里头半点光都没有。
雨水落在他面上,顺着眉骨、鼻梁一路淌下,看上去仿佛还有泪顺着流,却只是天地多事。
“是……是周成……”人群后面有人哆嗦着开口。
说话的是楚南生。
他刚才被人拦在外头,这会儿见空档子,硬是挤了进来,一眼就看见地上的尸体,脸色唰地一下白透。原本结实的膀子也微微发抖,整个人像烂了根的菜。
“你认识他?”钱道亨眉毛一挑。
“回老爷,学生楚南生,与周兄同院同房。”楚南生勉强稳住身子,依礼打了个躬,声音却有些发虚,“他……他今早还跟我说,题目再难,‘但求对得起胸中之学’……怎会,怎会……”
他说着说着,说不下去,眼圈竟有点红。
周围几个举子也低低议论起来:
“真是周成?”
“才前日还在茶铺里炫耀,说今年必取前列……”
“这才几日工夫,人就成了这副模样。”
权柄也好,鬼神也好,于这些口袋里只装得下几两银子的举子们来说,都太遥远。死,才是最让他们脚底发冷的东西——尤其这死者,昨日还与他们同桌抄题,如今却倒在井边,连眼睛都合不上。
“不许吵!”钱道亨沉声喝道,“再乱嚷,本官叫人把你们统统赶出去!”
嘈杂声一下小了许多,只剩雨声与几个胆小的人压抑不住的抽噎。
钱道亨缓了缓气,迈步走到尸体旁,强迫自己低头看了两眼。
乍一眼,他只觉得眼前一片惨白,心里“咯噔”一下:如果让京里的督学知道临川这么出人命案,一准要写折子——好了,说不定他这顶乌纱就得换人戴。
他不敢再想下去,只能尽量把声音压得稳定:“先验明死者身份,再查死因。楚举子,你上前认一认。”
楚南生咽了口唾沫,双腿发软,还是一步一步挪到尸体旁边。
他伸手,指尖在那冰冷的青布上停了一瞬,似乎是想拉一拉,又不敢真碰,最后只虚虚地握了握空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回老爷,是他,是周成。”
“好。”钱道亨点头,“在场有几位贡院举子作证——此尸确为西斋周成。”
四周零零星星应了几声“是”。
“你们都听好了。”钱道亨咳了一声,“此案关乎贡院清誉,本官必尽力查明。若有谁敢造谣传鬼,本官先以‘扰乱考试’之罪拿人!”
话虽这么说,眼角余光却扫到站在桃树下的一名老差役——那正是前两日被吓得发烧的巡夜人。此刻老差役缩在树阴里,半边衣袍都湿透了,脸色蜡黄,嘴唇轻轻哆嗦,一双眼睛却死死盯着井口,像怕那里面再次冒出什么。
“老刘。”钱道亨招手,“你过来。”
老差役犹豫了一下,只得硬着头皮挪到跟前,弯腰行礼:“老爷。”
“前日夜里,你在后院巡夜,曾听井中有哭声?”钱道亨问,“老实说。”
“是……”老差役嗓子干得发涩,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那夜……那夜风大雨急,小人巡到这里,听见井那头,有个女声哭。哭得……哭得心都跟着揪起来。小人以为是附近谁家女子出来偷会,想劝两句,便走近了些。”
他说到这里,眼中闪过一丝恐惧,忍不住抬手擦了把脸上的雨水,仿佛那夜扑在他脸上的井水又一次打来。
“你看到什么?”钱道亨耐着性子。
“起先啥也没见着。”老差役道,“井上盖着板子,周围空空的。小人喊了两声‘谁在那里’,没回音,就以为自己听错了,正要走,忽然——”
他打了个寒战:“忽然这井板下面‘哗’的一下,有水花溅起来,溅到小人脸上,冰得很。小人吓了一跳,脚下一软,跌在地上。那时候……那时候小人就看见,井口边缘,好像浮上来一张脸。”
众人屏住呼吸。
“脸?”钱道亨皱眉,“什么样的脸?”
“看不清。”老差役摇头,“那脸白得发亮,又没有眼睛嘴鼻,只贴在井边。小人当时腿都软了,只知道闭眼喊‘有鬼’。等旁边房里的师爷出来把我拖走,再看井口,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说着,自己也觉得有些心虚,垂着眼睛不敢看钱道亨的表情。
“你一个当差的,不好好巡夜,倒学起说书人来。”钱道亨冷笑,“你若说的是人,尚还有几分可信;若说是鬼,本官要问——你可曾见过鬼?鬼长什么样?也要遵礼法?”
老差役忙跪下:“小人不敢,小人不敢胡说。可这两日……这两日街上人都说,是三年前那柳家姑娘在井里哭,哭到今年,哭死了这位周公子。”
周围又是一阵低低的嗡嗡声,几个举子下意识地往后挪了挪。
沈砚站在人群边缘,听着这些话,心里却没起太多“鬼”的影子。他盯着周成的尸体,总觉得哪里不太自然,却又一时说不上来。
他缓缓走近几步,离草席不过两三尺的距离。
雨水顺着桃花枝条滴下来,落在死者的脸侧,那张脸被水雨一冲,原本的惊恐似乎被冲淡了些,却更添了一种说不出的空洞。
“敢问老爷。”沈砚忽然开口,“周公子是何时被捞上来的?”
钱道亨本就烦躁,听见他插嘴,差点当场喝斥,转念一想,贡院举子多少要照顾点面子,便板着脸道:“本官到前,仵作未到,是看井边脚印,估摸着不过一个时辰。你问这个做什么?”
沈砚道:“若是死前自行投井,或被人推入,照理说应有挣扎痕迹。学生斗胆,请老爷准许学生上前,替死者整整衣襟。”
钱道亨还未说话,楚南生已连忙道:“沈兄,你……”
沈砚回头,冲他安抚地一点头:“只是看一眼。”
钱道亨瞥见他眼里那抹镇静,心里微微一动——这穷举子倒有几分胆气,便挥了挥手:“去吧。不得乱动尸体骨节,待仵作来再细验。”
“是。”沈砚躬身,蹲下身去。
死者身上的青衫已经湿透,衣襟褶皱处有浑浊的井水痕迹,袖口泥污尤重。沈砚先把衣襟向内理了理,指尖触到那冰凉布料,连他这种向来自诩镇定的人,也忍不住打了个寒战。
他压下那丝生理上的排斥,顺势轻轻抬起尸体的一只手。
那只手僵硬而湿冷,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土,有的地方甚至嵌着细小的石渣,显见死前抓挠过井壁。
“有争扎。”沈砚在心里记了一笔。
更引人注意的是,死者的五指死死扣着什么东西,指节发白。沈砚试着一根根掰开,骨节间发出轻微的“咔嚓”声,旁边胆子小的举子听得头皮发麻,忍不住偏过头去。
费了好一番力气,那团东西终于露出全貌——是一片沾着泥的碎布。
碎布被水泡得发软,颜色也浮白了,然而隐约还能看出原本是淡粉色的绸料,上头绣着半朵桃花,针脚极细,花瓣层层叠叠,即便只剩半边,仍能看出绣功不俗。
“这是……”楚南生倒抽一口凉气,“绣坊的织……织物?”
有人脱口而出:“柳家姑娘当年最爱绣桃花。”
这句话一出,周围空气似乎更冷了一层。原本只是模糊的“鬼”故事,这会儿突然有了实物可以抓住,众人脑子里不免往最顺手的方向想。
“啧。”钱道亨拧起眉,“谁说的?谁见过?”
“老爷,小的见过。”站在外圈的一名老妪颤巍巍地挤上前来,身上披着打着补丁的蓑衣,头发被雨打得贴在额头,“当年那柳家姑娘给街坊大户绣帕子,桃花就是这么绣的。只不过人家正当花样年华,就这么……”
她话未说完,叹息声已经堵在喉咙里。
“住口。”钱道亨厉声,“旧事不必再提。”
他心里却十分清楚:这片绣花布若真与柳家姑娘有关,那这一口井的传言,只会越传越邪乎。
“把这布收好,暂做证物。”他吩咐衙役,“不可让人私自拿走。还有,那井——”
话说到一半,他突然瞥见井栏上似乎多了什么,眼神一凝:“嗯?”
“老爷?”旁边的小吏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一时没觉出异样。
沈砚还半蹲着,抬头一看,也愣了一下。
井栏靠近桃树的一段,石面上多了一行字。
那行字虽被雨水淋湿,却仍清晰可辨。字不多,只有七个,字体歪斜,却刻得很深,刀痕把石屑刮起一层,如今都被雨冲走,留下浅浅沟痕: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有人惊呼,“这不是那句……那句诗么?”
“崔护题都门的那句。”沈砚脱口而出,“‘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他念完,才觉自己失言,忙闭嘴。
四周却已经炸开了锅。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笑春风……”有举子喃喃重复,“好个‘不知何处去’。”
“这还用说?”另一个声音低低道,“柳家姑娘的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如今桃花仍开,她来索命,也合情合理。”
“住嘴!”钱道亨猛地一拍井栏,脸都涨红了,“再敢胡说,本官当场打你二十板!”
他这一声吼把众人吓得一激灵,议论声立刻小了下去,只有雨声仍旧不知好歹地哗啦作响。
钱道亨喘了几口粗气,强行压下心头的烦躁,转头看向一旁的书吏:“你去摸摸那行字。”
书吏被点到名,一脸苦相,只能硬着头皮上前,伸手在石上摸了摸,指尖刮过沟痕时,隐隐能感到石粉还未完全被雨水洗干净。
“老爷。”他回头,“这字不旧,刻得不久,至少……至少是这几日。”
“是今夜还是前一夜?”钱道亨又追问。
书吏为难道:“这……一时也说不准。若是昨夜刻的,遇上今夜的雨,也会被冲成这样。”
钱道亨沉下脸:“那就是说,有人趁夜来到井边,刻下这几句,之后不足两日,此井便有人投死?”
“是鬼,是鬼!”人群里有人忍不住低吼,“这不是鬼是什么?哪有人半夜跑来刻诗,刻完自己跳下去的?”
“或许有。”另一个声音冷冷插入。
众人循声看去,只见说话的正是沈砚。
他从地上站起身,袖口沾着一点泥水,却不去在意,目光仍盯着那行字,似乎在看什么。
“你又想说什么?”钱道亨有点不爽,却也再一次选择听听。
“学生只是觉得奇怪。”沈砚道,“若真是冤魂,有何必要用七个字告诉我们她‘人面不知何处去’?若是她要索命,只管来取,何苦还附庸风雅?”
有人忍不住噗嗤一笑,又立刻止住,生怕惹恼鬼神。
“你是说,这字必是活人刻的?”钱道亨眯起眼。
“学生斗胆猜测。”沈砚认真道,“一则,这字用刀,刀口在某几个转折处略有停顿,像是刻字的人边刻边想;二则,每一个‘桃’字、‘人’字的笔划都不一,若是鬼物借风雨写在石上,多半不必如此费力。”
他说到这里,又抬头看向那枝桃花:“第三,则是刻字之人偏偏选在这棵桃树之下,刻的是这句诗。若说不是刻给‘懂的人’看,学生实在想不出别的解释。”
他这番话说得不紧不慢,没有半点鬼神色彩,听在耳里,倒真像那么回事。
“懂的人?”钱道亨抓住这一句,“你是说,这字是在向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传话?”
“也可以说是在挑衅。”沈砚道,“或者提醒。”
他话音一落,四周又是一阵骚动。
书吏低声嘀咕:“挑衅谁?提醒谁?难不成……提醒那几个与柳家姑娘有牵扯的人?”
他本以为声音够轻,谁料临近的举子耳朵都不笨,话立刻像风一样传开,绕着井边转了两圈。
有人的视线不由自主落到楚南生身上,又移向其他几个平日里与周成来往密切的举子,那目光里,有恐惧,也有隐藏不及的偷觑。
楚南生被看得浑身不自在,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白,终于忍不住道:“你们看我作甚?我与柳家姑娘……只是远远见过几面,何曾说过一句话!”
“楚举子,没人说你。”沈砚缓声,“至少现在还没人。”
他这句半真半玩笑的话本想缓一缓气氛,谁知说着说着,连自己心头也沉下来——
三年前那桩“柳家姑娘”旧事,究竟波及了多少人?当年的读书人,今日散在临川各处,有的成了秀才、有的成了商贾、有的仍在考场上挣扎,有的……干脆做了死人。
而这一口井,像一只黑洞洞的眼,耐心地等着一桩桩旧事重新落回它的眼眶里。
“够了。”钱道亨一摆手,“旧事另查,不必在此嚼舌。本官看,此案暂按‘有人利用鬼神传言,借机行凶’立案,至于是自杀还是他杀,待仵作验尸再说。”
他说着,扭头对衙役道:“你们几个,先把周成的尸体抬到偏厅,用席子遮好,别叫雨再淋多了。再派人去他住的客栈搜查,有无遗书杂物。”
“是。”两名衙役应声上前,小心地把尸体抬起,放到担架上,草席重新盖上,把那张惊恐的脸遮了回去。
有人长出一口气,仿佛那青白的脸压在自己心头许久,终于移开了。
“井暂封。”钱道亨又道,“叫木匠明日一早再多钉几块板,把井口彻底堵死。至于那行字……”
“刮掉?”书吏试探着问。
“不。”钱道亨摇头,眼中闪过一丝精明,“先照样抄下来,报案卷用。石上的字留着,本官倒要看看,将来还有没有第二句、第三句。”
众人一听,背上不由又发凉。
抬尸的人走远了一些,井边渐渐空出来。老差役捂着胸口喘气,悄悄退到树后;那老妪则被另一名女眷扶走,嘴里仍旧念叨着“报应”二字。
雨又密了一阵。
沈砚看着那行刻字,手指不由自主地在侧边石栏上轻轻摩挲。石面粗糙,指腹被磨得有些生疼,他却像没觉,心里只在想——
刻字之人站在何处?他刻字的时候,是不是也被雨淋着?他刻完,是立刻走了,还是在井边站了一会儿,看看井里的水?那片绣花碎布,又是何时落到周成手中的?是在井边挣扎时抓住,还是早在别处便揣在怀里?
每一个问题,都像从黑井里伸出来的手,拉着他往深处去。
“沈举子。”
肩上忽然一沉。
他回头,看见掌柜的钱道亨——不,是知县大人,正阴着脸看他。
“学生在。”沈砚忙收回手。
“刚才你说的那些……不信鬼,信人。”钱道亨道,“本官记得。你既然敢在这么一群嘴里有一半信鬼的读书人面前说出这种话,便该知道,话说出去收不回来。”
他顿了顿,语气稍稍缓下来:“不过,本官也不讨厌你这种乱说话的人。明日午后,本官要在公堂上审这案子,你若不怕耽误考期,便来旁听。”
沈砚愣了一下:“老爷……许学生旁听?”
“你不是爱管闲事么?”钱道亨冷哼,“那就管到底。若你的嘴,能管出点有用的东西来,本官也不吝写一封书信给督学,说你‘心性坚毅,识见过人’。”
他话说得带刺,听在旁人耳朵里,十有八九会觉得是在讽刺,可沈砚却从中听出了另一层:至少,这位县尊不是只会忙着压案子。
他朝钱道亨郑重一揖:“学生敢不奉命。”
“别太得意。”钱道亨甩袖,“若让本官发现你只会添乱……连那封乡里给你写的荐信,本官都能顺手撕了。”
说完,他带着一干人等往前院去了。
井边一下子空了许多,只剩几个在雨中站得腿麻的举子还舍不得走,眼睛仍旧往那口黑井里瞄。
“沈兄。”楚南生挤过来,拉了拉他的袖子,“你方才那番话,把自己往火堆上送,你知不知道?”
“火堆?”沈砚回神,笑了笑,“案子燃起来,总得有人添几把柴。你怕被烤,我不勉强。”
“你就嘴硬吧。”楚南生苦笑,“说到底,你我不过是待考的小人物。这等命案,怎么轮得到我们掺和。”
“你不掺和,它照样发生。”沈砚看着他,目光却越过了他,落在那行字上,“而且,若真是有人借鬼神之名行凶……等那人杀完了该杀的,该不该杀的也就顺手杀了。”
他这话说得太轻,轻得像雨里的一个气泡,楚南生没有听真,只模糊地觉得心里一阵发凉。
“走吧。”沈砚撑起伞,“今晚这雨怕是还要下,站久了要受寒。明日还得进考场,总不能真让我们‘人面不知何处去’。”
“你还说这种话。”楚南生脸色一变,连忙朝井边拱了拱手,“柳家姑娘在上,有冤伸冤,无冤散去,千万莫在试场前找人……”
他念念叨叨的声音被雨声吞没。
两人从后院绕出去,学宫大门前的人群已经散了七七八八,只剩几个没住处的举子缩在廊下躲雨。街上的告示被雨水冲得更模糊,墨迹如同泪痕,从纸上慢慢垂落。
回到聚文斋时,天已经微微泛白。
刘仲果然守在门口,见两人回来,忙抢上前来,先是看他们有没有缺胳膊少腿,再问:“怎么样?真……真是周成?”
“是。”楚南生声音有些沙哑,“你明日若在考场上看见‘西斋周成’,那一定是鬼了。”
刘仲打了个寒战,往地上啐了一口:“呸呸呸,说什么鬼话。”
他一边把人往堂里让,一边又忍不住压低声音:“真闹鬼?”
“鬼很多。”沈砚笑了笑,“不过我只看见人。”
“你就爱卖关子。”刘仲瞪他,“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井里有没有白衣女鬼?桃花有没有自己掉进去?还有人说井栏上刻字……”
他话说到一半,突然止住。
因为沈砚已经走到窗前,伸手轻轻推开纸窗一角。
雨势似乎更小了,只剩稀稀落落几滴。天色在雨后的洗刷下模糊地亮了一些,巷子对面那棵瘦小的桃树,在微光里静静立着,花不多,枝条纤细,却努力开出几朵淡粉。
风从巷口吹来,把枝条轻轻一晃,树影投在对面墙上,恰好勾出一个女子的轮廓——长发垂肩,身形纤细,似站非站,又似回眸。
刘仲吓得一个激灵,险些坐到地上:“娘哎——”
“是树影。”楚南生看了一眼,强撑着说,“树影。”
沈砚也看了一眼,没有马上给出解释,只是把窗关上。
窗纸合拢,又将屋内与外头隔成两个世界。灯火尚在,案上的试卷也还摊着,只是纸边被湿气熏得微微卷起。
他坐回灯下,手仍旧有些冰凉。
笔被握在手里时,指尖有一点隐隐的刺痛——是刚才摸石栏时磨破了皮,还是掰开死者手指时用力过猛,他已经记不大清。只是那种疼痛提醒着他,方才的一切都不是梦。
“你还看得进去书?”刘仲有些难以置信,“都这个点了,离天亮没多久。”
“看不进去也得看。”沈砚低头,视线落在“以刑名为先”那几个字上,忽然觉得格外讽刺,“要不然,将来写判词的人,怕也是别有居心。”
他提笔,在空白处写下两个字——
“人心。”
墨迹未干,灯焰微微一晃,似乎也被这两个字惊了一惊。
窗外,雨终于停了。
只有远处学宫方向,那口旧井旁的桃树,还在滴水。每一滴水落下,似乎都带着一点看不见的影子,轻轻地,在井壁上、石栏上、刻字里,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