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时过半,滁州城无人入睡。
东门城楼上,陈沧澜和张煌言并肩而立,望着城外无边的黑暗。城下,四百多难民青壮像蚂蚁一样忙碌着——搬运滚木礌石的、修补城墙豁口的、往干涸护城河里埋设铁蒺藜的。
“王大人醒了。”张煌言忽然说。
陈沧澜转头:“情况如何?”
“脉象虚浮,但无性命之忧。”张煌言苦笑,“醒来第一句话就问:‘清军退了没?’我说退了,他点点头,说:‘那明日还会来。’然后就挣扎着要起来,被大夫按住了。”
“王大人……”
“他让我转告你,”张煌言看着陈沧澜,“‘能守则守,不能守则退。人比城重要。’”
陈沧澜沉默。
城墙下传来争执声。两人循声望去,是陈安和一个瘸腿老人——白天自愿加入巡逻队的那个。
“你这腿,连路都走不稳,怎么搬石头?”陈安急道。
“搬不动大的,搬小的。”老人指着地上那些拳头大的石块,“一块也是搬。”
“老爷子,这不是儿戏!清军打来,您这身子……”
“我三个儿子都死在北边了。”老人打断他,声音嘶哑,“老大死在潼关,老二死在开封,老三……就死在我眼前,替我挡了一刀。”
他弯腰,抱起一块石头,身子晃了晃,但站稳了。
“他们死的时候,我没在身边。今天在滁州,我在。”老人抬头看着陈安,“小伙子,让我做点什么。不然到了下面,我没脸见他们。”
陈安张了张嘴,最终没再劝,只是默默帮他把石头搬到墙根。
陈沧澜收回目光。
“这样的人,城里还有多少?”他问。
张煌言没回答,只是递过来一本册子。
陈沧澜接过,借着火把光翻开。册子是周师爷刚整理好的,记录着愿意参与守城的难民名单,后面简单标注着背景:
**刘老三,徐州铁匠,妻女死于乱军,右手三指断。愿守城。**
**赵小虎,十六岁,猎户之子,父死于逃亡路。箭法尚可。**
**周瘸子(本名不详),六十二岁,原凤阳卫军户,三子皆战死。腿瘸,但能扔石。**
**王氏(女),三十一岁,扬州绣娘,全家死于扬州十日。愿缝补衣甲、煮饭。**
**孙寡妇,二十八岁,丈夫原为滁州卫小旗,去年剿匪战死。识得令旗,可助传令。**
……
一共四百二十七人,每人都有故事。每段故事背后,都是破碎的家,死去的人,和不肯熄灭的火。
陈沧澜合上册子,还回去。
“你打算怎么守?”张煌言问。
陈沧澜走到城墙边,指着下方:“清军若来,主攻方向必是东门——刘千户带兵从这里逃跑,清军一定知道此门最弱。所以我们要在东门外多做文章。”
“什么文章?”
“陷阱。”陈沧澜说,“干涸的护城河是天然的陷阱区。我已经让陈安带人在河道里挖了三十个陷坑,坑底插竹签,抹了粪毒。坑与坑之间,撒满铁蒺藜。陷坑表面用芦苇、浮土掩盖,夜间看不出来。”
张煌言点头:“清军骑兵若冲锋,第一波就会栽在河里。”
“不止。”陈沧澜指向城外更远处,“从三里外到护城河,这中间是开阔地。我让难民把家里所有能用的破锅烂铁都拿出来了——砸碎,磨尖,撒在地上。马踩上去,必跛。”
“这是……”张煌言眼睛一亮,“《武经总要》里记载的‘蹄刺阵’!”
“对。虽然简陋,但能拖慢骑兵速度。”陈沧澜又指向城墙,“城上,每五十步设一个滚木礌石点,共十八处。每处配五人:两人负责推滚木,两人负责扔礌石,一人负责观察、指挥。”
“热油和石灰呢?”
“集中在三处城墙塌陷点内侧。”陈沧澜说,“那是清军最可能突破的地方。一旦墙体被破,立刻泼洒,然后火把扔下去——油遇火即燃,能烧出一片火墙。”
张煌言听着,手指在城墙垛口上轻轻敲击,像在推演。
“弓箭手如何布置?”
“赵小虎挑了三十个会用弓的,都是猎户出身。我把他们分三队,每队十人,在东、北、西三面城墙机动。”陈沧澜顿了顿,“但箭矢不够。库房里只有三百支箭,分下去每人不到十支。”
“省着用。”张煌言说,“等清军进入五十步内再射。射人先射马——马目标大,倒了还能绊倒后面的。”
两人沉默片刻。
“还有一件事,”张煌言低声说,“周师爷刚才来报,说城里有内奸。”
陈沧澜心头一紧:“确定?”
“不确定,但有迹象。”张煌言指向城内某处,“今天傍晚,有人看见两个陌生人在粮仓附近转悠,形迹可疑。守仓的衙役去盘问,他们说是逃难来的,但口音不是北边,倒像……南京那边的。”
“南京?”陈沧澜皱眉,“南京的人来滁州做什么?”
“不知道。但那两人看见衙役就跑了,没抓到。”张煌言说,“王大人昏迷前交代,要小心内应。清军攻城,常先派细作混入城中,或刺探军情,或放火制造混乱。”
陈沧澜环视城内。夜幕下的滁州城,点点灯火如星。但谁知道哪些灯下,藏着想开门迎敌的人?
“我去查。”他说。
“小心。”张煌言按住他的肩,“敌暗我明,不要打草惊蛇。”
陈沧澜点头,正要下城,忽然听见——
鼓声。
不是城里的鼓,是从城外传来的。
低沉、缓慢,像巨兽的心跳。
一下,又一下。
城头上所有人都停下手里的活,望向城外。
黑暗里,什么也看不见。但鼓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
“是战鼓。”张煌言脸色发白,“清军在集结。”
陈沧澜冲到城墙边,极目远眺。远处地平线上,隐约有火光蠕动——不是几支火把,是成片成片的,像燎原的野火。
“多少人?”陈安也上来了,声音发颤。
“至少……三千。”陈沧澜说。
三千对五百。
不,连五百都没有。能战的,只有衙门五十个衙役,卫所一百多老弱,加上四百多刚摸兵器的难民。真正能拉弓射箭、提刀拼杀的,不超过两百人。
而城外,是三千清军。
鼓声停了。
死寂。
然后,号角声响起——苍凉、悠长,像狼群对月长嚎。
火光开始移动,分成三股。一股往东门来,一股往北城墙,还有一股……往南山方向。
“他们发现小路了。”陈沧澜心往下沉。
张煌言也看到了:“巡逻队呢?”
“在山上。”陈沧澜咬牙,“二十个人,挡不住。”
“那怎么办?”
陈沧澜盯着那股往南山移动的火光,脑中飞快计算。
南山小路陡峭,清军不可能大规模行军,最多派一两百人尝试绕后。但如果被他们绕过去,从背后袭击,城就完了。
“我带人去堵。”他说。
“带多少人?”
“五十。”陈沧澜说,“东门和北墙更需要人。五十个,够了。”
“太少了!”张煌言急道。
“山路窄,人多没用。”陈沧澜已经转身,“陈安,挑五十个身手最好的,要敢近战的。带上所有能用的刀,半刻钟后,南门集合。”
“是!”
陈沧澜冲下城楼,经过校场时,看见赵小虎正带着三十个弓箭手在分箭。
“赵小虎!”
“大人?”
“带上你的人,跟我走。”
“可是东门……”
“东门有张大人。”陈沧澜说,“南山更需要弓箭手。”
赵小虎没再多问,挥手召集人手。
半刻钟后,南门下,八十个人集结完毕。
五十个刀手,三十个弓手。火把光照着一张张年轻或苍老的脸,每个人眼里都有恐惧,但没人退缩。
陈沧澜站在队伍前,只说了一句话。
“清军想从背后捅我们刀子。我们去告诉他们——此路不通。”
然后他推开南门。
门外是黑黢黢的山道,像一张等着吞噬的嘴。
南山没有名字,只是滁州城南一片连绵的丘陵。所谓小路,其实是采药人、樵夫踩出来的兽径,最宽处不过三尺,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涧。
陈沧澜带着八十人,举着火把,沿山路向上攀爬。
山路难行,不少地方需要手脚并用。陈沧澜走在最前,山河剑背在身后,手里握着一根长矛——这是从卫所库房找到的,枪头锈了,但总比空手强。
爬到半山腰一处平台时,他抬手示意停下。
平台不大,约莫三丈见方,是山路上一处难得的开阔地。往前,路分两条:一条继续向上,通往山顶;一条向左拐,绕向城北。
“就是这里。”陈沧澜说,“清军若想绕后,必走左边这条。我们在此设伏。”
他快速分配任务:“赵小虎,带你的人上右侧峭壁,找掩体埋伏。等清军进入平台,听我号令放箭。”
“是!”
“陈安,带二十个刀手,守在平台入口,清军一进来就堵死退路。”
“明白。”
“剩下三十人,跟我守在平台出口。清军冲过来,死也要挡住。”
八十人迅速散开,隐入黑暗。
陈沧澜靠在平台出口的一块巨石后,屏息倾听。
山下,清军的号角声隐约传来。但山上很静,只有风声和虫鸣。
时间一点点过去。
陈沧澜握紧长矛,手心全是汗。这是他第一次指挥伏击战,第一次要决定八十个人的生死。
他想起父亲教剑时说的话:“剑客对决,胜负往往在一念之间。但战场不同——战场上的胜负,是许多人许多个‘一念’的累积。你要做的,不是让自己那一念完美,而是让所有人的一念,都往同一个方向。”
现在,这八十个人的“一念”,都系在他身上。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
然后他听见了——脚步声。
很轻,很密,像雨点打在树叶上。不是一两个人,是成队的,至少有几十人。
清军来了。
陈沧澜从石缝中看去。
黑暗里,一队黑影正沿山路摸上来。没有火把,显然是想悄无声息地绕后。人影绰绰,看不清具体人数,但看移动的阵型,大约七八十人。
果然是精兵。
领头的是个矮壮汉子,一手持刀,一手扶着山壁,脚步极稳。他每走几步就停下来,侧耳倾听,确认安全后再前进。
谨慎,老练。
陈沧澜屏住呼吸。
清军队伍缓缓进入平台。平台不大,七八十人进来,立刻显得有些拥挤。领头的那人停在平台中央,环顾四周,似乎在判断该走哪条路。
就是现在。
陈沧澜举起右手,猛地挥下。
“放箭!”
峭壁上,三十张弓同时发射。
箭矢破空的声音在夜色里格外刺耳。清军猝不及防,瞬间倒下一片。惨叫声、惊呼声、中箭的闷响混在一起。
“有埋伏!”领头那人吼道,“退!快退!”
但退路已经被陈安带人堵死。
二十个刀手从平台入口的阴影里冲出来,刀光在黑暗里闪烁。清军前队想后退,后队还在往前挤,一时间乱作一团。
“往前冲!”领头那人见退路被堵,当机立断,“冲过去!”
剩下的五六十个清军朝平台出口涌来。
陈沧澜站起身。
“杀!”
三十个刀手从他身后冲出,迎向清军。
两股人潮在山路上撞在一起。
没有阵型,没有章法,就是最原始的搏杀。刀砍在肉上的闷响,骨头断裂的脆响,临死的惨叫,混杂成地狱的乐章。
陈沧澜挺矛上前。
一个清军挥刀砍来,他侧身避过,长矛顺势刺出——不是刺胸口,是刺大腿。矛尖从大腿侧面刺入,穿出,那清军惨叫着倒地。
陈沧澜抽矛,血溅了他一身。
第二个清军从侧面扑来,他来不及回矛,左手拔出腰间的短刀,反手一挥。刀锋划过咽喉,血喷出来,滚烫。
第三个、第四个……
他像一头冲入羊群的狼,每一击都致命。山河剑法在战场上转化为最简洁的杀人技——刺喉、穿心、断筋、破腹。
但清军太多了。
他带来的三十个刀手,转眼倒了七八个。一个少年被砍中肩膀,刀嵌在骨头里拔不出来,另一个清军补了一刀,少年倒下,再没起来。
那是白天挑兵器时,说“我爹教过我射箭”的那个少年。
陈沧澜眼睛红了。
他长矛横扫,逼退两个清军,然后纵身前扑,短刀直刺领头那人的胸口。
那人反应极快,举刀格挡。两刀相撞,火星四溅。
“好身手!”那人用汉语说,声音嘶哑,“可惜了。”
他刀法凶狠,每一刀都势大力沉。陈沧澜的短刀太轻,不敢硬接,只能游斗。
但山路太窄,没有腾挪空间。
三招过后,陈沧澜被逼到悬崖边。身后就是深涧,深不见底。
“下去吧!”那人一刀劈下。
陈沧澜侧身,刀锋擦着胸前划过,割裂衣襟。他趁机一脚踢向对方膝盖。
那人闷哼一声,单膝跪地。陈沧澜短刀再刺,但对方左手突然从靴筒里拔出一把匕首,刺向他小腹。
躲不开了。
陈沧澜咬牙,不躲不避,短刀继续前刺——以命换命。
当一支箭射来。
“噗!”
箭矢从侧面射入那清军太阳穴,箭头从另一边透出。那人动作僵住,瞪大眼睛,手里的匕首停在陈沧澜腹前半寸。
然后他缓缓倒下。
陈沧澜抬头,看见峭壁上,赵小虎正放下弓,脸色煞白。
“大人!小心后面!”
陈沧澜回头,又一个清军冲来。他来不及起身,就地一滚,短刀向上撩,划开对方腹部。肠子流出来,那清军惨叫着倒地。
战斗在那一刻突然停了。
清军还剩二十多人,但领头的死了,退路被堵,前路不通。他们聚在一起,背靠背,警惕地看着四周。
陈沧澜这边,三十个刀手只剩十五个,人人带伤。陈安那边也倒了几个,但入口还堵着。
峭壁上,赵小虎的弓箭手重新搭箭,箭尖指向下方。
“降者不杀。”陈沧澜站起身,抹去脸上的血。
清军互相看看。
一个年轻的清军忽然扔下刀,跪地。然后第二个,第三个……
最终,二十三个清军投降。
陈沧澜让陈安带人把他们绑了,押下山。自己留在平台上,看着满地的尸体。
八十个清军,死了五十多个。自己这边,刀手死了十五个,伤了八个。弓箭手无人伤亡。
赢了。
但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他走到那个死去的少年身边。少年眼睛还睁着,望着夜空,手里还紧紧握着刀——一把生锈的刀,刀刃崩了好几个口子。
陈沧澜蹲下身,合上他的眼睛。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旁边一个受伤的刀手。
那刀手捂着肩膀的伤口,哑声说:“他……他没说过。只说家里人都死了,就剩他一个。”
陈沧澜沉默。
他站起身,看向山下。
滁州城在夜色里,像一座孤岛。城东、城北,火光冲天——清军主力开始攻城了。
号角声、战鼓声、喊杀声,隐隐传来。
这里的战斗结束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带着俘虏和伤员下山时,天边已泛起鱼肚白。
南门下,张煌言亲自带人接应。看到陈沧澜一身血,他脸色变了。
“伤哪了?”
“皮外伤。”陈沧澜摇头,“山上解决了,七八十个清军,俘虏二十三个。”
张煌言松了口气,但看到后面抬下来的尸体,笑容又消失了。
“十五个……”他喃喃。
“不止。”陈沧澜说,“陈安那边也死了三个。一共十八个。”
十八个。
昨天还活生生的人,今天就成了冰冷的尸体。
“把他们……好好安葬。”张煌言说。
“没时间了。”陈沧澜指向东门方向,“那边情况如何?”
“清军主力在攻东门。”张煌言脸色凝重,“已经攻了一个时辰。城门暂时没破,但守军伤亡不小。滚木礌石快用完了,热油也泼了三锅。”
“我去东门。”
“你……”
“我还能战。”陈沧澜打断他,“南山这边,交给你。俘虏审一审,看能不能问出清军部署。”
张煌言点头:“小心。”
陈沧澜转身要走,张煌言又叫住他。
“陈公子。”
“嗯?”
“活着回来。”张煌言看着他,“王大人说,人比城重要。这话,对你也适用。”
陈沧澜笑了笑,没回答,提着染血的长矛,朝东门奔去。
穿过街道时,他看见难民区的窝棚里,百姓都出来了。他们站在路边,看着一队队伤员被抬下来,看着陈沧澜满身是血地跑过。
没有人说话。
但他们的眼神,陈沧澜看懂了——那是祈求,是绝望,也是最后的希望。
跑到东门城楼下时,他听见了震耳欲聋的撞击声。
“咚——咚——咚——”
是冲车在撞门。
每一次撞击,整座城楼都在震颤。灰尘簌簌落下,梁柱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陈沧澜冲上城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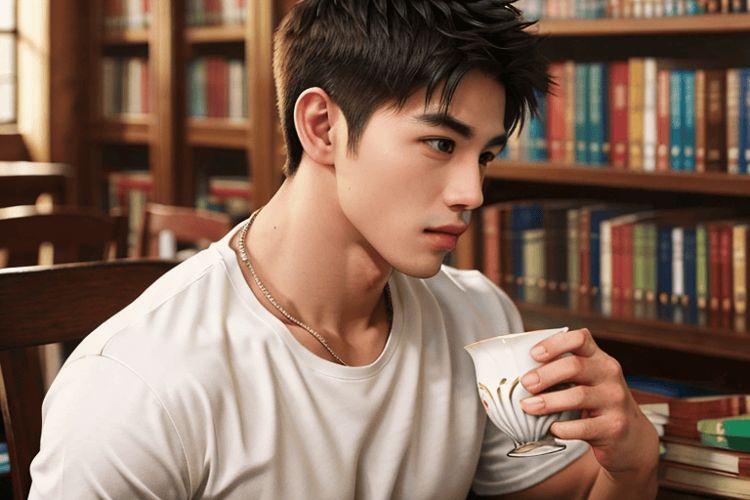
眼前的景象,让他呼吸一窒。
城外,清军如蚁。
密密麻麻的步兵方阵堵满了视野,至少两千人。他们举着盾牌,顶着箭雨,一波接一波地往城墙下冲。云梯已经架上城墙,清军像潮水一样往上爬。
城头上,守军正在死战。
滚木礌石早就用完了,现在守军只能用刀砍、用枪捅、用手推。一个衙役刚把一架云梯推下去,就被另一架云梯上来的清军一刀砍中,栽下城墙。
惨叫声被淹没在喊杀声里。
陈沧澜看见周师爷——那个胆小怕事的师爷,此刻正抱着一块石头,哆哆嗦嗦地朝城下砸。石头砸偏了,没砸中人。一个清军爬上城头,举刀朝他砍去。
陈沧澜长矛掷出。
矛从那个清军后背刺入,前胸透出。清军倒下,周师爷瘫坐在地,脸色惨白。
“师爷,下去!”陈沧澜吼道。
“不、不……”周师爷爬起来,捡起地上的刀,“我……我也能战!”
他双手握刀,朝另一个爬上来的清军砍去。刀法毫无章法,但用尽全力。那清军举盾格挡,刀砍在盾上,火星四溅。
陈沧澜没时间管他,冲到一个缺口处。
这里正是北城墙的三处塌陷点之一。沙袋垒的墙体已经被撞开一个大洞,清军正从洞里往里涌。守在这里的十个难民青壮,已经死了六个,剩下四个在苦苦支撑。
陈沧澜拔剑。
山河剑出鞘,剑光如雪。
他一剑刺穿第一个清军的咽喉,抽剑,反手削断第二个清军的手腕。第三、第四个清军同时扑来,他侧身,剑画圆弧——“山河剑法”第四式“环山河”。
剑光掠过两人的脖颈,血喷如泉。
剩下的清军被他的悍勇吓住,攻势一缓。
“堵住缺口!”陈沧澜吼道。
四个幸存的难民青壮回过神来,搬起地上的沙袋、砖石,往缺口处堆。但清军又冲上来了。
陈沧澜守在缺口前,一剑一个。
但清军太多了,杀不完。
一个清军从他侧面突入,一刀砍向他后颈。陈沧澜挥剑格挡,但另一个清军从正面刺来长枪。他避无可避——
一杆长枪从旁边刺出,架开了那致命一击。
陈沧澜回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是刘老三,那个脸上有疤的铁匠。
他手里拿着一杆不知从哪捡来的长枪,枪法毫无章法,就是捅、扫、砸。但力气极大,一枪能捅穿清军的盾牌。
“大人,我来帮你!”刘老三吼道。
“好!”陈沧澜点头,“你守左,我守右!”
两人背靠背,守在缺口前。
剑光与枪影交织,血肉横飞。
不知杀了多久,陈沧澜的手臂开始发麻。剑越来越沉,每一次挥动都需要用尽全身力气。
刘老三更惨,他身上已经中了三刀,血流如注,但还在坚持。
“老三,下去包扎!”陈沧澜吼道。
“不……不行……”刘老三喘着粗气,“我一走……缺口就守不住了……”
他话音未落,又一波清军冲来。
这次人更多,至少有二十个。他们看准了这个缺口,要一举突破。
陈沧澜握紧剑,准备拼命。
但就在这时,城下传来鸣金声。
清军攻势一顿。
然后,如潮水般退去。
退得很快,很突然。
陈沧澜愣住了。
刘老三也愣了:“他们……退了?”
“不对。”陈沧澜看向城外。
清军确实在撤退,但不是溃退,是有序后撤。退到一里外,重新列阵。
然后他看见了——清军阵中推出五门火炮。
黑色的炮身,在晨光里泛着冷光。
“是炮……”刘老三声音发颤,“他们……要轰城了。”
陈沧澜的心沉到谷底。
刀剑可以挡,箭矢可以防。
但炮……
滁州的城墙,只是夯土包砖,不是南京那种巨石垒砌的坚城。五门炮,不用多,只要轰上半个时辰,城墙必塌。
而他们,没有任何反制手段。
“完了……”旁边一个难民青壮瘫坐在地,“这下真的完了……”
陈沧澜没说话。
他只是看着那五门炮,看着炮口缓缓抬起,对准了滁州城。
晨光刺破云层,照在城头上。
新的一天开始了。
也许是滁州城的最后一天。
他握紧剑,剑身上的血已经凝固,变成暗红色的痂。
父亲说,剑是死的,人是活的。
但现在,人好像也快死了。
那剑呢?
剑还能做什么?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一件事——
只要他还站着,剑就不会倒。

![[沧海遗龙]小说无删减版在线阅读_沧澜陈怀远全文免费无弹窗阅读_笔趣阁](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fb4c9853ce01389b61a1d40ea11881b.jpg)
![结婚十年,我刷到妻子给肇事司机庆生全文免费无弹窗阅读_笔趣阁_[林舒李哲]全章节免费阅读-爱八小说](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518671cb08a3364b6a34707c61bfb1b.jpg)

![知青夫妻的逆袭路全文+后续_[苏禾王桂芬]后续无弹窗大结局-爱八小说](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016891dc740ba6e306ad785798b02b8.jpg)
![[求婚当天,白月光抢婚,我的舔狗女友笑了]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苏柔林清月]全文+后续-爱八小说](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0d38238210483eed98fee0c5acf7f1a.jpg)
![妈妈发工资总给我抹掉一个零,我杀疯了全章节免费阅读_[叶总晓雅]全文+后续-爱八小说](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8f077aa7abf0ad5b971bb9aa195b32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