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战场所受之伤突然恶化,
嘴唇乌紫,口吐鲜血,御医说必须尽快剔腐肉清余毒。
我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娘子飞鸽传书,
她是医仙在世,也是唯一有希望救母亲的神医。
娘子收到飞鸽传书,二话不说快马加鞭,
马车开到中途,她却说临时有伤民要救治,回不来了。
我绝望蹲在太医院的长廊里,给她发去一道又一道加急传书。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的呼吸声越来越微弱。
第九十九道飞鸽传书,她终于回了。
只有两个字:“已归。”
我等了好久,等到了她的小师弟,
拿着她用她那双金贵的手为他绣的荷包,以及近乎挑衅的话语:
【今天出了小小意外,师姐不仅没怪我,还鼓励我了呢。】
我才知道,原来她说得临时有伤民要救治是帮小师弟收拾烂摊子。
她在我最绝望的时候,抛下了我,去陪了别的男人。
母亲咽气那刻,我的心脏也仿佛停止了跳动。
太医院的御医们满头大汗安慰我。
“我们尽力了,墨凌,节哀顺变。”
大家看我的眼神里有安慰,更多的是怜悯,
毕竟所有人都清楚,唯一能给母亲解毒的柳烟此刻正在安抚她的小师弟。
1
我抱着母亲冰冷的身体,枯坐了一夜。
直到天光大亮,我派去药王谷的亲卫终于回来了,却只有他一人。
他跪在地上,不敢抬头,声音都在发抖:
“少爷,夫人她……她不肯回来。”
我的心猛地一沉,“为什么?”
“林……林公子在和夫人闹脾气,他嫌夫人陪您的时间太多,冷落了他。”
“前日不小心割破了手指,便一直哭闹不休,夫人……夫人正在哄他。”
割破了手指。
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我的母亲,镇国大将军,
身为一个女子,为国镇守边疆三十载,
身上大小伤口上百处,正命悬一线时,
我的娘子,却因为她的小师弟割破了手指,便置我母亲的性命于不顾。
多么荒唐,多么可笑。
第九十九只信鸽终于飞了回来。
它的腿上,绑着一个小小的竹筒。
我颤抖着手,解开了竹筒,倒出里面的字条。
上面是柳烟熟悉的、温柔清秀的字迹,
却像一把淬了毒的利刃,狠狠扎进我的心里。
“初礼已无大碍,明日即归。勿念。”
勿念。
好一个勿念。
我看着字条,又低头看了看怀中死不瞑目的母亲,忽然就笑了。
母亲,儿子不孝,没能为您请来神医。
但儿子向您保证,从今日起,这世上,再无医仙柳烟。
2
母亲下葬那天,天灰蒙蒙的,像是被一层陈旧的布盖住了。
我抱着那个沉甸甸的紫檀木盒子,里面装着我母亲,
那个为国征战一生的铁血娘子,如今只剩下这点温热的灰烬。
回到空无一人的将军府,我刚将骨灰盒在灵堂正中的桌案上放好,柳烟就到了。
她依旧是一袭白衣,纤尘不染,
清冷的眉眼间带着一丝风尘仆仆的倦意,看起来像是急着赶回来的。
可她终究是迟了。
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瘦弱的男子,是她的小师弟,林初礼。
他亲昵地挽着柳烟的手臂,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这座肃穆的府邸,仿佛在逛什么新奇的园子。
“阿凌,我回来了。”
柳烟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带着她独有的,能安抚人心的力量。
可惜,如今的我,心已经死了。
我没有看她,只是平静地开口,声音嘶哑得我自己都觉得陌生:
“柳烟,我们和离吧。”
空气瞬间凝固。
柳烟脸上的温和褪去,
换上了一丝无奈和不悦的浅笑,像是看着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阿凌,别闹了。”她说,
“我知道你生气我没能及时赶回,但用这种苦肉计来逼我,就没意思了。”
她甚至还想伸手来拉我,被我侧身躲过。
我抱着母亲的骨灰盒,一字一句地告诉她:
“母亲,她等不到你了。”
柳烟的眉头皱得更深,眼底的不耐烦几乎要满溢出来:
“墨凌,你为了逼我回家,连这种谎话都说得出口?”
她根本不信。
她怎么会信呢?在她心里,
我大概永远是那个为了她一点垂怜,就能摇尾乞怜的狗。
“师姐,你看,我就说世子殿下是骗你的吧。”
她身边的林初礼终于开了口,声音小小的,说出的话却像淬了毒的针,
“女战神将军威名赫赫,吉人天相,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呢?”
“世子殿下也真是的,为了让师姐你回来,竟然拿自己的母亲来开玩笑。”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那双看似无辜的眼睛瞟着我,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意:
“不过这将军府也真是配合,演得跟真的一样,
冷冷清清的,连个下人哭丧都没有,未免也太不走心了。”
我死死地盯着他,胸口翻涌着滔天的恨意。
我等着柳烟开口呵斥他。
哪怕只有一个字。
但她没有。
她只是默许地看着林初礼,甚至还安抚性地拍了拍他的手背,
然后才转向我,语气里带着高高在上的失望:
“阿凌,闹够了就跟我回去,别让初礼看了笑话。”
那一刻,我心中最后一丝名为“夫妻情分”的弦,彻底断了。
我笑了,抱着怀里冰冷的骨灰盒,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原来,我母亲的死,我撕心裂肺的痛,
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一场为了争风吃醋而上演的,拙劣又可笑的闹剧。
我的笑声让柳烟和林初礼都愣住了。
我止住笑,用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死寂般的眼神看着他们。
“明日,灵堂设在正厅。”
我的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
“我母亲,等着你们来上柱香。”
2
我娘的灵堂就设在将军府的正厅。
来吊唁的宾客不多,都是娘生前的至交,个个神情肃穆。
这片肃穆,却被林初礼尖利的声音划破。
“墨凌,你别演了,将军吉人自有天相,怎么可能就这么去了?”
“我看你就是为了逼我师姐回家,才串通了御医,演了这么一出苦肉计!”
他站在灵堂中央,对着满堂宾客,言之凿凿。
我看着他,没有说话。
我娘的牌位就在那里,黑色的棺木停在厅中,
一切都那么真实,真实到刺痛我的每一寸皮肤。
而我的娘子,柳烟,就站在林初礼身边,
沉默着,用一种审视的、带着一丝不耐的眼神看着我。
她的沉默,就是默许。
林初礼见我没反应,胆子更大了。
他忽然笑了起来,那笑容天真又恶毒。
“既然世子说将军已经仙逝,那骨灰坛里装的,应该就是将军的骨灰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径直走向灵台。
我的心猛地一沉。
“你想干什么?”
“不干什么,”林初礼回头,冲我天真一笑,
“我就是想验证一下。如果将军真的不在了,那咱们就放一场烟花送送她。”
“用骨灰做的烟花,一定很别致,很壮观吧?”
“骨灰烟花”四个字,像淬了毒的针,狠狠扎进我的脑髓。
我疯了。
我脑子里最后一根名为理智的弦,应声而断。
我娘戎马一生,护国佑民,尸骨未寒,竟要被人如此羞辱!
“你敢!”
我嘶吼着,像一头被逼到绝境的恶兽,疯了般朝他扑过去。
可我没能碰到他。
一只纤弱但有力的手臂,
从侧面死死箍住了我,将我牢牢地禁锢在原地。
是柳烟。
她的手勒得我生疼,冰冷的声音贴着我的耳朵响起,没有一丝温度:
“墨凌,别再闹了。”
别再闹了?我闹?
我看着她,想从她那张貌美无俦的脸上找出一丝一毫的心疼或不忍,
可什么都没有。
只有冷漠,和一丝被我搅扰了清静的厌烦。
就在我被她死死抓住的这一瞬间,林初礼已经抱起了灵台上的骨灰坛。
他甚至还对着柳烟露出了一个得意的、邀功似的微笑。
然后,他当着所有人的面,揭开了坛口的盖子。
“住手!”
我用尽全身力气挣扎,可柳烟的禁锢纹丝不动。
她只是冷眼看着,仿佛眼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一场与她无关的闹剧。
林初礼笑着,手腕一斜。
那盛着我母亲骨与血、荣耀与一生的灰白色粉末,
就这么被他尽数倾倒进了灵前燃烧着纸钱的火盆里。
“轰——”
火光猛地窜起三尺高,无数被热浪卷起的灰烬,
夹杂着我娘的骨灰,在空中飞溅、飘散,像一场盛大而悲哀的嘲讽。
整个灵堂,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被这疯狂的一幕惊呆了。
我忽然就不挣扎了。
我停止了所有动作,就那么静静地,任由柳烟抓着我的手臂。
我慢慢地转过头,用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死水般的眼神,看向她。
柳烟似乎被我的眼神刺了一下,下意识地松开了手。
我没有理会她,也没有再看林初礼一眼。
在满堂宾客惊愕的注视下,我缓缓抬起手,
从宽大的素白袖袍中,抽出了一卷被明黄色绸缎包裹的东西。
那是我用母亲一生的赫赫战功,在母亲咽气前,向陛下求来的最后一道恩旨。
我展开圣旨,清冷的声音不大,
却清晰地传遍了灵堂的每一个角落,一字一顿,字字如刀。
“柳烟,林初礼,接旨。”
3
灵堂之上,死一般的寂静。
前一刻还死死钳制着我的柳烟,此刻像是被烫到一般松开了手。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或者说,是看着我手中的圣旨,眼神里充满了荒谬与错愕。
“墨凌,你……你又在玩什么把戏?”
她的声音干涩,却依旧带着那份高高在上的审视。
我没有回答她,只是将圣旨高举过头。
“柳烟,林初礼,接旨。”
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劈开了灵堂内凝滞的空气。
宾客们纷纷后退,哗啦啦地跪了一地。
只有柳烟和林初礼还僵立在原地。
一个尖细却威严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
“大胆柳烟、林初礼,见了圣旨,为何不跪!”

随着话音,一名身着藏青色宦官服饰的老太监从人群后走出,
他身后跟着两列手持金瓜的御前侍卫,甲胄森然,杀气腾腾。
是皇帝身边的李公公。
林初礼腿一软,当即瘫倒在地,抖如筛糠。
柳烟的脸色终于变了。
她可以不信我,但她不能不认得宫里的人。
她缓缓屈膝,那双曾为我诊脉、为我梳洗的手,此刻却撑在地上,微微颤抖。
李公公从我手中接过圣旨,清了清嗓子,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镇国将军墨晴,乃国之柱石,开国元勋,一生戎马,功在社稷……其子安乐世子墨凌,深明大义,以母之不世之功,换朕今日之诏,以清君侧,以正国法,朕,准之!”
李公公顿了顿,锐利的目光扫过跪在地上的柳烟。
“御赐医仙柳烟,身为世子妃,蒙朕厚恩,享万民敬仰。
然,国之柱石病危,召之不回;其夫泣血求告,视若罔闻。
为一介竖子微末小伤,置家国重臣生死于不顾,致使将军抱憾而终。
此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其心可诛!”
“今,朕下诏,夺去柳烟‘医仙’封号,贬为庶民!”


![[王爷,和离书已烧]后续超长版](https://image-cdn.iyykj.cn/2408/541ab800bd9944ff6c8faa795fa24083.jpg)
![[我好心捎带同事上下班,却遭停职审查]小说无删减版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f0289c4d647cd2ef10ba0c387e03b50.jpg)

![[冷战期,看到老婆和白月光热吻]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01cff761c720acc84a3dfc22bae6ed0.jpg)
![支教女老师违反校规出校门后,悔疯了在线阅读_[蒋欣欣张黎明]最新章节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41ed078894f86ae58ee2bc0d1498abd.jpg)


![「地球Online离婚版,我抽中SSR」免费阅读_[乔宁苏宴礼]后续完整大结局](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1cec199abb8c88d7d8d19251389aada.jpg)

![[君子风度是假的!他对我早已沉沦]后续已完结_「沈静灵堂」无弹窗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a2e889cc31fa56d6eebefa7dc311c582.jpg)



![[被囚五年后,前妻她杀疯了]后续全文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5197684dcfce9e844a36a3120f54673f.jpg)

![[丈夫说私生子可以继承家业后,他悔疯了]更新/连载更新](https://image-cdn.iyykj.cn/2408/9858d568bec132080fe155b09a7183b6.jpg)


![[挖井三年丈夫拿井水让青梅洗澡后,我将他赶出家门]全文免费无弹窗阅读_笔趣阁](https://image-cdn.iyykj.cn/2408/f5bd02f5068628e80f0613c06ccc98fc.jpg)
![[围裙与高跟鞋的和解]后续已完结](https://image-cdn.iyykj.cn/2408/912e905179721db7016923e99e2bb8ca.jpg)

![[初见大佬误终身,他将我强势锁定!]最新后续章节在线阅读_[沈暮辞宋辞]全章节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eaadfdfcc8e91505abc6b1e56080357.jpg)

![[见家长那天,女友竟然把竹马也带了过来]番外](https://image-cdn.iyykj.cn/2408/582311b6f6d109329f7420be455417f9.jpg)


![[高p婆婆爱网恋]全章节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6abaf0ae5e40568a86e7f84da76cfbae.jpg)


![重生1979:逆袭人生从打猎开始全文在线阅读_[宋晨沈千雅]全文+后续](https://image-cdn.iyykj.cn/2408/28cea6d7645217382bbc56db1fda6dcc.jpg)





![[念安不渡云舟远]小说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34a73f584ff277eb8bf9fe5cc60ac1a.jpg)


![[女儿过生日,婆婆被人当成小三揍了]后续已完结](https://image-cdn.iyykj.cn/2408/97bfa9947a8c8513d2a010d48dc8c361.jpg)
![[惊遇火车上的变态男]最新章节免费阅读](http://image-cdn.iyykj.cn/0905/391f8e90a1bfb351e53e110781c09cadd4f691ca793a21-20acRZ_fw480webp.jpg)

![「分手后开民宿,女房客全部沦陷了」完结_[米高杨思思]抖音小说](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131ae5ea3ebadc689a86a9bd9dc826e.jpg)
![「饥荒破船中,我的系统能钓万物」最新章节列表_[陆北小鱼]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3292acfbca4af64c7da36a6d9c7149c5.jpg)
![[重回我爸妈的高中时代]小说无删减版在线阅读_姜景辰姜止小说后续在线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66651e1c828a46503579f1278663b55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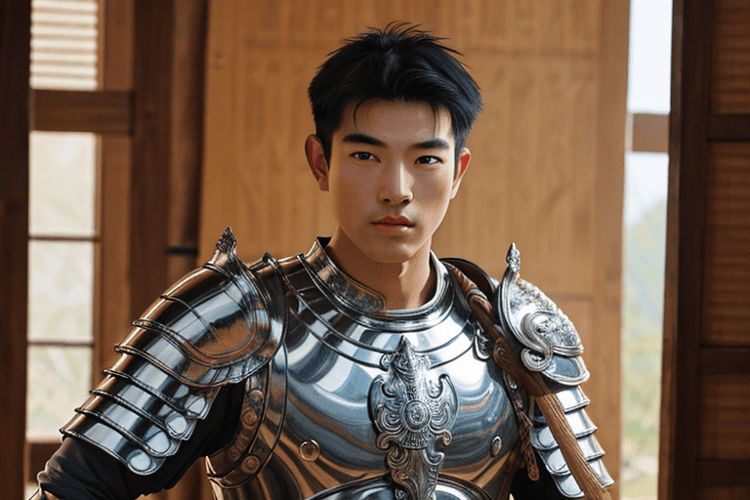

![[地球Online离婚版,我抽中SSR]无弹窗阅读_「乔宁苏宴礼」小说无删减版在线免费阅读](http://image-cdn.iyykj.cn/0905/1acbe69ab2aaa9dce0d8f541de26844d30b34c3c20fdd0-tXWnbv_fw480webp.jpg)
![[谁说娇气包没人要?我偏偏就要宠她]电子书_「陆屿苏玉」全章节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725c65a82d4ff10e52e63cac22140aa5.jpg)




![[不做攀附骨血的吸血鬼]后续完结版](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eea268c29506166b3110d91d4cfd7eb.jpg)
![[留下离婚协议后,顾总失控求复合]免费阅读_姜眠小说无删减版在线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862faadadae89f3efcd165c4678f162.jpg)
![[房东半夜要我赔空调,我杀疯了]完结](https://image-cdn.iyykj.cn/2408/1a1207f693fa418c9f78f4c4317e6808.jpg)






![[她名四月]完结版免费在线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c86a3afb58ae93714c6e5d2cc3723467.jpg)
![[我撕碎闺蜜白莲花的伪装]无弹窗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462e95894a3de613d2f9f2cb6305d103.jpg)
![白眼狼全家吸我血?我转身投靠反贼免费阅读_[谢云枝谢松岚]小说全文txt完整版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08ddea848c382dbbeaa00874fec5f8d0.jpg)
![[专治各种不服!恶人作妖我拳头伺候]全文+后续_姜生秦淮茹最新章节目录番外+全文](https://image-cdn.iyykj.cn/2408/7ea26d78c75f26f43cee8753db1e15ec.jpg)

![[过期热恋]全文+后续_[周秉言宁羽]完结版免费阅读](https://image-cdn.iyykj.cn/2408/7db527ebd739e2e44841e1187644ccca.jpg)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