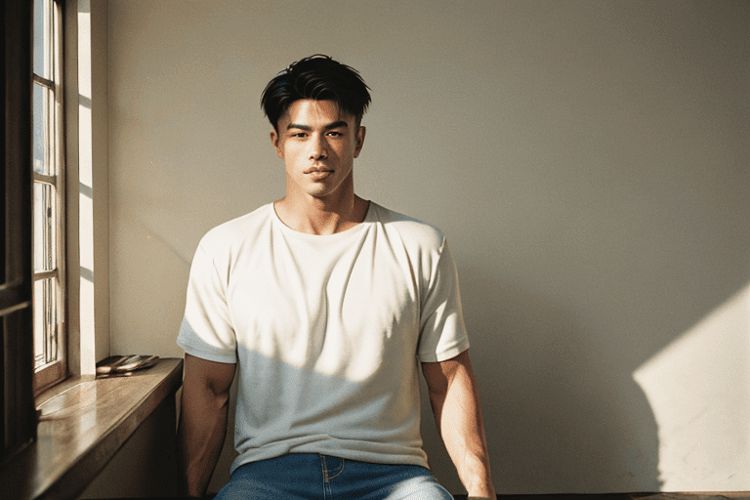数学课上的那场辩论,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陈暮晓的心底漾开了层层涟漪。傅瑾瑜最后那句坦诚的认可和那张写着“逻辑更胜一筹”的纸条,被她小心翼翼地夹在了最常用的数学笔记本扉页。那不仅仅是一句赞美,更像是一种信号,标志着他们之间的关系,从纯粹的成绩竞争,悄然过渡到了一种带着惺惺相相惜意味的、更复杂的阶段。
周五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的铃声终于响起,宣告着短暂周末的开始。教室里瞬间被一种解放般的躁动填满,同学们迫不及待地收拾书包,商量着晚上的安排或是周末的放松。
陈暮晓不紧不慢地整理着书本,将需要带回家的试卷和习题册仔细地放进书包。她的目光不经意地瞥向斜前方那个座位,傅瑾瑜也已经收拾妥当,正将最后一只笔放进笔袋,动作依旧从容有序。
自从图书馆和数学课之后,她发现自己开始不自觉地留意他的动向。这是一种微妙的变化,隐秘而难以言说。
她背起沉甸甸的书包,随着人流走出教学楼。傍晚的阳光褪去了午后的灼热,变得温柔而金黄,透过香樟树层层叠叠的枝叶,在灰色的水泥路面上投下细碎而晃动的光斑。这条从教学楼通往校门的香樟道,是许多走读生放学的必经之路。
五月的风带着初夏的暖意,拂过道旁茂盛的香樟树,树叶发出沙沙的轻响,那特有的清苦香气愈发浓郁,沁人心脾。陈暮晓推着那辆有些年头的浅蓝色自行车,汇入了放学的人流。车轮碾过地面,发出轻微的辘辘声。
就在她准备跨上车座时,眼角的余光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也推着车,从旁边不远不近地跟了上来。是傅瑾瑜。他骑的是一辆黑色的、款式简单的山地车,和他的人一样,透着一种低调而利落的感觉。

两人的车辙,几乎是同步地,并排印在了洒满夕阳余晖的香樟道上。
陈暮晓的心跳莫名快了半拍。这并非刻意同行,只是回家的方向大致相同,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这种并行的状态。她下意识地调整了一下车把,让自己保持在一条直线上,既不想离得太近显得刻意,也不想离得太远显得生疏。
一开始,是长久的沉默。只有自行车链条转动的声音、车轮碾过路面的声音,以及周围同学们的喧闹声作为背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尴尬,或者说,是一种正在试探和酝酿的张力。
傅瑾瑜似乎也没有要主动开口的意思,他只是目视前方,安静地骑着车。夕阳将他挺拔的背影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路面上。
最终还是陈暮晓,试图打破这种令人心慌的沉默。她想起数学课上那道题,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话题。
“那个……傅瑾瑜,”她侧过头,声音不大,但足够让他听见,“今天课上那道题,你后来提到的那种几何性质,是不是在高等数学里会有更系统的阐述?”
傅瑾瑜闻声,微微侧过头来看她。夕阳的金光落在他侧脸上,勾勒出清晰的轮廓,连他脸上细微的绒毛都看得分明。他的眼神依旧平静,但少了平日的淡漠,多了一丝专注。
“嗯。”他应了一声,声音在傍晚的风中显得比在教室里柔和一些,“涉及到一些微分几何的初步概念,比如曲率。不过用初等数学的视角去理解,也是一种锻炼。”
他的回答很实在,没有炫耀高深的知识,而是肯定了她在现有知识框架下的思考。这让陈暮晓放松了不少。
“曲率……”她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这个陌生的词汇,感觉眼前似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听起来很奇妙。所以数学的世界,真的没有尽头。”
“学无止境。”傅瑾瑜言简意赅地总结,目光重新看向前方。
话题似乎又要中断了。但这次,沉默不再那么难熬。他们并排骑着车,穿行在光影斑驳的香樟道上。风吹起陈暮晓额前的碎发,也吹动了傅瑾瑜敞开的校服外套衣角。
过了一会儿,傅瑾瑜却主动开口了,他指着路边一根电线杆顶端:“你看那只鸟。”
陈暮晓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只灰喜鹊正站在电线杆顶端,歪着小脑袋,好奇地打量着下方川流不息的学生和车辆,时不时发出几声清脆的鸣叫。
“它好像在看热闹。”陈暮晓忍不住轻笑了一下。她没想到傅瑾瑜这样的人,也会注意到路边的鸟儿。
“嗯。”傅瑾瑜的嘴角似乎也极轻微地向上牵动了一下,快得像是错觉,“像不像我们上课时,老周站在讲台上看我们的样子?”
这个突如其来的、带着点冷幽默的比喻,让陈暮晓愣了一下,随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她想象着严肃的老周变成一只歪着脑袋的灰喜鹊,站在讲台上俯瞰众生,这个画面实在有些滑稽。她笑得眼角微微弯起,连日来积压的疲惫似乎都随着这笑声消散了不少。
傅瑾瑜看着她明朗的笑容,目光在她弯起的眼角停留了一瞬,然后也转过头,眼底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
这个关于小鸟的插曲,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两人之间那扇无形的门。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
他们开始断断续续地聊天。话题依旧围绕着学习,但范围拓宽了许多。从一道物理题中涉及的洛伦兹力聊到宇宙速度,从一篇语文课的文言文聊到历史中的某个典故,甚至偶尔会提及最近看过的一本有趣的课外书。
大多数时候是陈暮晓提问或发起话题,傅瑾瑜言简意赅地回答或补充。他的话依然不多,但每一句都言之有物,逻辑清晰。陈暮晓发现,褪去“年级第一”的光环和课堂上的冷静犀利,私下里的傅瑾瑜,其实并不难相处,甚至有种独特的、属于理工男的幽默感,只是表达方式非常含蓄。
他们聊着天,车轮保持着一致的节奏,并肩前行。夕阳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两个影子时而靠近,时而分开,随着车辆的移动和光线的角度不断变换着形状。
有时,会遇到需要避让的行人或车辆,他们会默契地同时减速,或者一个稍稍领先,另一个随后跟上,很快又恢复并排。这种无需言语的默契,让陈暮晓感到一种奇异的安心。
她偷偷侧目观察他骑车的样子。他骑得很稳,背脊挺直,目光专注地看着前方,但神情是放松的。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也毫不在意。这个样子的傅瑾瑜,比在教室里那个一丝不苟的学霸,多了几分少年人的鲜活气息。
她注意到他握车把的手,修长而有力,指节分明。想起图书馆和讲台上那两次短暂的指尖触碰,她的耳根又有些微微发热。
他们就这样骑着车,聊着天,穿过了大半个城市。香樟道走到了尽头,转入更宽阔的马路,两旁的建筑从学校变成了居民区和商铺。周围的同学渐渐稀少,最后,这条回家的路上,仿佛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和两辆并排前行的自行车,以及车轮下两道同步延伸的、浅浅的车辙。
在一个需要分岔的路口,傅瑾瑜缓缓停下了车。陈暮晓也跟着停了下来。
“我往这边。”傅瑾瑜指了指左边的路。
“我往右边。”陈暮晓说。
短暂的沉默再次降临,但这次,沉默里没有了尴尬,反而有种意犹未尽的余韵。
“下周一见。”傅瑾瑜看着她,声音平静。
“嗯,周一见。”陈暮晓点点头,感觉自己的心跳又有些加快。
傅瑾瑜没再说什么,只是对她微微颔首,然后蹬动自行车,向左边的路口驶去。他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渐渐变小,最终消失在街角。
陈暮晓站在原地,没有立刻离开。傍晚的风温柔地吹拂着她的脸颊,空气中似乎还残留着他身上那股干净的皂荚味,混合着香樟树的气息。她低头看着地面上刚刚印下、还未被其他车辆覆盖的两道车辙,它们曾那么近地并行了一段长长的路。
这一路,没有激烈的竞争,没有刻意的靠近,只有自然而然的同行,和偶尔交汇的思维火花。那些关于洛伦兹力和电线杆上小鸟的对话,那些无声的骑行默契,比任何正式的交流都更让她感到一种心灵的贴近。
她忽然觉得,那条通往高考的、充满压力的漫漫长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沉默而优秀的同行者,似乎不再那么孤单和难熬。
她深吸一口气,空气中满是夕阳和香樟树的温暖味道。然后,她骑上车,转向右边的路口。嘴角,不自觉地扬起了一个轻松而柔软的弧度。
香樟道上的同步车辙,终将各自延伸向不同的方向。但这一路并肩的风景,和那份悄然滋长的、混合着欣赏、默契与淡淡悸动的情愫,已经深深地印刻在了这个初夏的傍晚




![[揭穿爸爸出轨后,我被妈妈塞进洗衣机]最新章节免费阅读-爱八小说](https://image-cdn.iyykj.cn/2408/b7f5ee47e4a950ef0fae526247751c10.jpg)
![[雾里天涯,晚风将至]小说后续在线免费阅读-爱八小说](http://image-cdn.iyykj.cn/0905/5fdf8db1cb13495420bb7e08bd2f7b54d0094aa7.jpg)